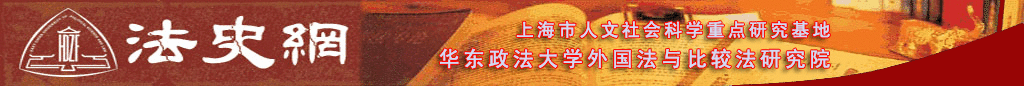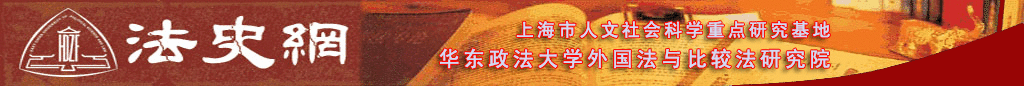【中文关键词】 票据习惯;票据市场;近代中国;票据
【摘要】 近代中国,随着现代银行业的进入,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票据习惯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向着统一的趋势迈进。然而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一些具备鲜明地方特色的票据习惯仍在各地继续通行,形成一副立体的多元混合架构图。市场、社会与政府形成一种合力,形塑着票据习惯的发展路径,引导着票据习惯的发展方向,为我们呈现出一条自主开放的法律成长途径。
【全文】
票据[1]历史悠久,从周朝的质、剂,唐朝的“飞钱”,宋时的“交子”、“会子”,到明清时期的会票、银票,无不是市场与货币发展的直接体现,被认为是中国除四大发明外的又一大发明{1}(P.258),诸多票据习惯也随之形成。18世纪以降,随着票号、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外资银行、官商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发展,票据使用日益普遍,票据习惯呈现出强烈的统一要求和趋势。然而新制未成,旧习未消,一些固有票据习惯仍继续通行于各地,形成中西杂糅、新旧纷陈的多元局面。这一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影响力量为何?既往研究对此少有分析[2]。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和探讨,以期能拾遗补缺,为当下的票据制度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一、票据市场与票据:从杂乱走向统一
自有票据问世以来,就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票据市场,且随着票据使用的普遍而不断发展。然而由于传统中国长期未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商业市场,票据使用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限制,因而显得非常庞杂。明清时期我国各地通行的票据种类繁多,有会票、凭贴、兑贴、上贴、上票、壶瓶贴、期贴、信票、店号票、钱票、庄票等,名称各异,形式也各有不同,通行区域也有别。即使是同一种票据,也内分多种。譬如会票,据钱币专家俞鸿昌的研究,现存可见的清代会票有手写凭贴、执照、兑票、信票等种类{2}。
19世纪中后期,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习用票据发生新的变化,本票和支票等新式票据开始出现并使用。20世纪初,随着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在各大商埠城市的设立,当今所谓三大票据——汇票、本票和支票逐渐在全国流通开来。但一些本地票据仍继续通行于各地,使得票据种类仍很繁杂。譬如近代上海习用票据主要有庄票、支票、存票、拆票、汇票五种{3}(P.489)。南京通行的票据有便条、本票、汇票三种;苏州通行的票据则有本埠割条、定期存票、他埠汇票、本埠支票等;镇江通行的票据有汇票、庄票、期票、拨条、钩条、信汇{4}(P.1-29)。北京的习用票据有汇票、借据、兑条、存条、划条;天津习用票据有汇票、期条、存条、借据、土票;杭州习用票据主要有庄票、汇票、支票三种;厦门有二联式过单、办房单、二联式收单、收条、二联式汇票和三联式汇票;芜湖习用票据有汇外埠票、定期借款票、买米支票、本街钱庄流通票;太原习用票据有定期存单、存条、寄存条、汇票、借约、押券、支票、取款证{4}(P.37-131)。汉口一些大钱庄通用的票据有庄票、上条、钱条、汇票、划条、拨条等{5}。习用票据和票据市场的庞大杂乱略窥一斑。
虽然各地习用票据种类很多,并不统一,但汇票、庄票等票据却已然在全国流通,成为通行票据,将银行和钱庄、本地与外地资本连贯起来,乃至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资本市场——“申票”市场。[3]中国近代票据市场因而呈现出有主有次、主次分明的图景。当然,此图景基本是在市场力量的自我推动下绘就的,并且有着统一的趋势。然而,这一趋势的最终完成却依赖于行政力量的干预。1929年,民国南京政府制定颁布《票据法》,明确规定汇票、本票和支票为法定票据。通行票据庞杂的局面至此终告结束,归于统一,但现实中,一些票据仍时有使用,譬如上海钱庄直到1932年仍在发行庄票{6}(P.224)。
在票据市场从杂乱向统一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市场流通主体的票据,其基本要素也呈现出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趋势。
首先,票据的发行日渐趋向统一。比如清代广泛使用的会票,早先的出票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如钱庄、商铺等。19世纪前后,随着钱庄、票号的兴起,因其雄厚的资本金和很高的信誉,逐渐垄断了会票的发行。20世纪初,新式银行在全国各大商埠普遍建立,会票遂改称为汇票,其发行权统归于钱庄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形制规格上也逐渐统一,成为通行全国的主要票据。银钱票也是如此,在早期并非票号和钱庄专属,其他行业店铺也会发行。乾嘉之后,逐渐统归于钱庄和票号。20世纪初,民国政府实行货币改革,改两归元,银钱票的使用范围不断缩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票据发行的统一,对于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资本市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作用。
其次,票据的功能不断趋向完备。以会票为例,会票是由出票人或机构发出,约定由自己或委托人(店铺、钱庄、票号等机构)见票后履行所确定的经济内容的有价证券,其主要功能就是异地汇兑{7}。陆世仪在《论钱币》中即记载有当时江苏一些商人需要携带巨额金钱去京师,因道路不便,即“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8}张集馨也曾称其三叔“进京与邑人郑健堂太守之子平山诸生借银二千两,又与西贾借银数千两,捐纳双月知县,会票来家兑还”{9}(P.6)。此外,清代会票还有信贷功能。清初小说《豆棚闲话》中所记徽商汪兴哥在苏州因经营不善而需增资,因此“寻同乡亲,写个会票,接来应手。”{10}是类记载颇多,兹不赘述。可以确认的是,在市场需求的强力推动下,会票已被用作异地资金支付的凭证,使用日常化了。19世纪初,山西票号兴起,专营汇兑业务,且由于“票号结交官场,是以存资日富”{6}(P.15),会票成为票号发行的主要票据,有汇兑、信贷、汇划清算等诸多功能,在票据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票据功能的完善,扩大了票据的流通范围,为票据市场的统一提供了前提。
再次,票据权利的保全措施日益周密。票据的早期保全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其一,采用传统取信方法,在票券上标注“见会”、“凭中”、“中”等字样,并注明利息,以第三方“中人”为担保,通过“合符”或“合券”方式来确认和保护票据权利。其二,在票面上注明兑付方法、使用的平码,避免相互扯皮。其三,票据发出方在票面上钤盖自家特有印记,或数字,或图章,以鉴别真伪。“为了防止伪造,每张纸币在发行之前都被铺在一份作为存根的账本上,然后发行者在纸币与其下面空白纸张的连接处打上自己商号或者钱铺的印记,另外再随意地画一些线条,纸币上有一部分,空白纸上也有一部分。这样,存根上留下的每张做了记号的页码总数与所发行的纸币数量恰好相等。这种方式虽然原始和粗陋,但对于防止伪造假冒纸币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11}(P.272)
19世纪以降,随着票号的发展,全国性的资本市场基本形成,票据使用愈发普遍,其保全技术也愈加精密。譬如山西票号发行的会票,其保全措施有:采用特殊印纸——特制麻纸,统一印制;采取水印技术,在票据上印制特殊印记;由专人用毛笔书写,其字迹在各总号和分号备案留存,同时加盖特制印签;创设密押,汇款金额设有专门的银暗号,日期也有专门的月暗号和日暗号,并定期更换{12}(P.681)。从票据材料的选取到印制,再到内容的书写和密押的设置,形成完整的票据保全链,有力保障了票据功能的实现,便利于其流通。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发现在票号存续期间发生过因保全技术问题而使款项被冒领的案例。毋庸置疑,票据保全技术的发展,不仅保障了票据发行方的利益,也保护了执票人的利益,有利于票据市场的发展和票据习惯的完善。
第四,票据的形制日益完善。以会票为例,形制由文字和图形组成。图形一般为柜形框图、官格纸型,上为盖头、下为柜体,中分条格;其内书写兑票人、付款方、款数、日期,以及“凭贴付与去人”、“存贴后照”等惯语,并加盖有抬头章、钱名章、压数章、具名章、号码章、日期章、审核分类登记章、年号印记、讨保印记等{2}。票号兴起后,开始印制会券(即会票),规格统一,内容规范{12}(P.121)。会票的形制逐渐统一完善,三联式成为会票的主要流通款式。票据形制的完善,促进了票据的流通和票据市场的统一。
当然,也有例外情形。譬如银钱票,虽使用日广,但版式却一直比较简陋,且各地不一致。光绪庚子之前,京师通行的银钱二票,为票号、钱店、香蜡铺发行。钱票宽二寸许,长约五寸,中记钱额,盖方印,左角又盖发行各铺之图记{13}(P.2293)。“钱票一项,各处常有,惟各店各式终不一律。”[4]直到20世纪20年代,汉口银票仍一般用行书书写,骑缝处盖章,为不记名式票据{14}(P.443)。
最后,票据市场的发展、票据的完善,意味着近代中国票据信用的发达。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庄票的信用度在中外贸易中并不高,当时各洋行买办就有为庄票担保的职责,因为西方商人并不认可庄票{15}(P.80)。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受货币紧缺影响,庄票使用日益普遍,信用度不断提高。不仅外商利用钱庄票推销洋货,华商和洋商间的资金周转也依赖于庄票{6}(P.18-20)。当时怡和洋行就经常用庄票的方式在上海和香港之间汇寄资金{16}(P.92)。无疑,庄票信用度的提高是与上海开埠以后,钱庄将发行庄票作为主营业务,重视维护庄票信用有着紧密关系{17}(P.4-5)。而随着信用度的提高,庄票不仅流通日广,而且功能增多,成为钱庄和外资银行之间的银钱汇划票据。信用是票据的基石。近代票据信用的日渐发达,为票据的完善、票据市场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在市场和行政的双重作用下,票据市场从杂乱逐渐走向统一有序,一个相互联通的全国性市场已然成型。票据的发行、形制与保全、功能等不断完善,信用日益发达,统一的趋势显明。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各地习用票据不尽一致的现象却非短期内可以消除,近代票据市场和票据呈现出鲜明的共性与个性并存的特点。
二、票据习惯:从粗陋迈向完备
中国近代票据市场的不断发展,票据要素的日益完善,也带动了票据习惯的进步。
中国票据的功能自始就被设定为现金输送,以发行人的信用为担保,因而其不仅是有价证券,同时也是信用证券。明清时期,票据使用并不普遍,票据习惯相对较少,也比较简略。由现存的康熙年间会票可以看出,其时会票上有“见票即兑”、“见票兑付”、“验票兑付”字样的,还有“三月内准兑”、“四月终兑”、“六月内兑付”字样的,前者表示该会票是即期票,后者则是远期票{7}。钱庄发行的庄票同样也有即期、远期之分,只是远期票的时限缩短为5日、10日、20日,后又规定“至多以十日为限,不得再迟”{18}(P.110)。这种即期、远期的区分和规定,以及不记名票据(如银钱票、庄票)承兑时“认票不认人”的惯例等,即是早期的票据习惯。此外,清代的一些会票还可以辗转相授而不取钱,是介于会票和钱票之间的具有双重性的货币。{19}由于此时期的票据全凭商家信用为保障,因此容易滋生滥发虚票、辗转磨兑的弊端,引发社会混乱。清政府对此也只是采取严查严惩的行政手段,其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并未严禁票据使用,更没有建立相应制度进行管理引导,治标不治本。当然,这一举措无疑是与当时政府的国家治理方略有关,认为些许钱物“细务”,无关国家大政。
政府的放任自流,迫使银钱业不得不自发行动起来,成立钱业公所等行业组织,实行行业自治。钱业自治机构的成立,固然是出于维护行业自身利益的目的,但也不乏规范行业行为,维持秩序之意图。因此,虽然各地通行的票据习惯仍有着鲜明的本地特色,但在钱业公会的努力下,也呈现出不断完备的发展趋势。下面就以庄票的挂失止付和票据清算为例来加以论说。
庄票系无记名式票据,有定期和即期之分,其上如注明期日,则为定期,如未注明期日,则为即期。由于钱庄信用卓著,庄票具有代替实际货币的功能,且由于商业习惯,庄票于钱庄破产清理时,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一旦所有人遗失庄票之后,其合法权益极易被侵害。为保护票据所有人和银庄的合法利益,尽量减少纠葛,银钱业逐渐形成一些行业习惯法则。
早在1841年,上海县在钱业请求下,勒石告示,“如有拾取庄号往来银票,即行送还,听凭照议酬谢,毋许争多论少,致起讼端。倘敢故违,许即禀县,以凭饬提拾票人,从严惩治,决不宽贷”{20}(P.130-131)。此时尚没有挂失一说,钱业借助政府,通过勒刻碑石,禁止冒领庄票。此规定实根据《大清律例?户律?钱债》中“得遗失物”条而立,但有所变通,将律例中“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21}(P.266)的规定改为“遗失票银千两,有人拾取送还,酬谢银十两;视票银多少增减。”{20}(P.130)就银钱业来看,这一调整无疑是合适的,兼顾了各方的权益。因为庄号往来银票大额居多,若按律例“拾者给半”,则无论对庄号还是失主来说都有失公平;而给予拾票送还者一定的酬谢则不仅是物质奖励,而且照顾到他的心理感受。当然这一规定很简单,只针对遗失这一种情形,未做更细致区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避免好事之徒捡到庄票后,强为顶认,致成讼端,表现出国人畏讼、怕麻烦、强调刑罚威慑的法律心理。
19世纪末,报纸等新式传媒在中国沿海和沿江城市普及开来,登报声明挂失已成为一种通行的做法。1900年,上海钱业重整条规,并登报立案。该条规对庄票的挂失止付情形做了粗略区分,规定:“议行用庄票,来踪去迹,皆可根查。凡挂失之票,或被窃盗,或遭水火不测,或是遗失,曾经登报存案作废,均准止付,可由失票之人,觅保立据收银。”如“查系自受愚骗,票入人手,或已付庄,或已买货,查明确实,有帐可稽,有货可指者,不能止付。”{6}(P.678)同时,对于拾票送还者,仍沿袭1841年的惯例。两相比较,1900年的规定无疑要细致得多,不仅区分了不同的挂失情况,而且对庄号止付也有明确规定,庄号、失主的责任权益有了清晰界定。无疑,这种变化是与时代发展相同步的,一方面,新式经济生活方式如登报声明挂失对行业习惯法则产生重大影响;但本土习惯法则,如中国传统经济生活中的取信方法“觅保立据”等并未被废除,仍继续保留,发挥作用。
此后,上海钱业就有关规定进行了多次修正和补充。1906年,上海南北市钱业重新修订条规,对“觅保立据收银”进行了修正,增加“保人必须付银之家熟悉相信者,出立保据,方可付银,以杜后患”的规定{6}(P.680)。此规定弥补了失主和保人之间私下合谋的漏洞,进一步保护了庄号的利益。
1917年,钱业公会成立,重新修订业规,在1906年规定的基础上又有修正:“各业行用庄票,来踪去迹,虽可根查,如真被盗窃或遭水火不测,确系遗失,曾经登报存案作废者,均暂止付,须过100天后由失票之家觅保收银,并向商会存案。惟保人必须付银之家熟悉相信者,出立保据,方准付银,以杜后患。如监守自盗者,不在此例。”{6}(P.683)此次修正不仅延长了庄号兑付银两的时限,更明确要求向商会备案;并增列了庄号免责的情形,建构起比较完备的庄号权益保护体系。
1923年,上海钱业公会修正的上海钱业规则第13条对挂失止付办法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庄票关系信用甚巨,不论何人,凡执有庄票者,视为现款。倘往来户向庄家出立庄票或已付款,或已买货,或已贴现,查明确实有帐可稽,有货可指,及自受愚骗,票入人手,或监守自盗,并另有别种关系,不论何时,不得向庄家挂失止付。如实被水火盗窃,或确系遗失,由失票人出具证书,向庄家请求挂失止付,并登中外著名报纸各一份,声明作废,一面向地方官厅存案,得暂时止付,即由庄家将款项送交本公会,暂为保存。过一百日后,毫无纠葛,失票人可觅殷实保证人,或殷实庄号,出立保证书,再行付款。但保证者须为庄家所信任。倘另有纠葛,被庄家查出,虽请求挂失止付,不生效力。如未挂失之先,票已照付,庄家不负责任。如已挂失,并照本项规定之手续,一一办妥,庄家之款业已付出者,对于任何方面亦不负丝毫责任,其挂失之庄票,不论存没,均作无效。”{6}(P.698-699)与此前历次修正相比,此次修正不仅细致地规定了庄票挂失止付的具体程序和各种情况下的处理措施,还明确了庄票所有人、占有人,以及付款人的权利义务。尤其是对所有人和占有人之间的权利区分,与欧洲罗马法系中有关动产占有的法律精神有着惊人的暗合。虽然一属民法规定,一为商事习惯规定,但两者在法理上有着相对的一贯性。[5]
从1841年至1923年,上海钱业有关庄票挂失止付的规定日渐完善,其变迁轨迹清晰可见。同时,上海银钱业的这些规定也为其他城市学习或援用。譬如芜湖银钱业对于票据遗失,应由执票人商请前途止兑,并登报声明,倘或发生纠纷,亦由声请止付之人自行交涉解决之;天津、北平、烟台等地对于汇票兑款,在票面上盖有“面生讨保”或“无保不付”等戳记,以昭慎重{22}(P.98)。票据挂失止付习惯由一地扩展至多地,统一趋势已很显明。
票据的清算是银钱业清理票据的一种经营行为。早期,各地银钱业之间因为往来的票据不多,银钱的收解量不大,多是采取直接轧账即“汇”的方法进行票据清算,并将现银解送,以了清账目。然而在上海,由于钱庄同行家数多,划拨次数太繁复,极易发生错误。于是有从业者费尽心思,想出了公单清算的办法{6}(P.494)。凡满500两的收解改用公单记数,500两以下仍各解送现银,后来,凡满100两亦用公单记数,称为小公单。大小公单可通盘抵冲,各庄汇划亦凭公单收付。同时在钱行内设立汇划总会办理划拨清算工作,各庄只要将公单送至汇划总会名曰“交公单”,汇划总会职员将各庄公单互相抵冲,按差额通知各庄或收或付,以现银结算{6}(P.496)。此后,随着金融联系愈加紧密,为保障信用,防范风险,钱业公会对公单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如收付公单无论拆票、还拆、汇头、收票各款,均须互打公单,不得以收付轧过;总会拆出银两亦须各打公单,不得以空白纸头书写;公单上数目字必须明白大写,不得潦草;总会一进一出,均须实行打公单作数,不得作收解论;小同行汇来汇去公单,均须上门去打,不得自行加添;小同行汇头须注明某庄名下,以便查考;取消大小公单,无论多少连同零数均打一纸公单,每日轧清等{6}(P.497)。如此一来,钱庄间的票据清算就简便多了,权利责任也更加明晰。
1941年,鉴于同业间收解数字剧增,钱业准备库要想当天结清公单很困难。于是钱业召集各庄代表,成立公单问题研究委员会,研究改良公单制度。在各庄代表的集思广益下,乃有“差额报告单”制度的出现。“差额报告单”制度由同业收票通知单、同业收票回单、差额报告单三种单据组成,各回单表示当日应收款总数,各通知单表示当日应付款总数。钱庄将本庄应收应付总数和收付差额则填入差额报告单相应栏内,并将“差额报告单”送交钱库,轧收时以送款簿存入钱库,轧付时则开钱库支单,同时交钱库以所收各庄回单,备钱库查核,通知书则留庄备查,不交钱库{6}(P.498-500)。与前述公单制度相比,“差额报告单”无疑要简便而准确得多。从现金收解到公单清算,再到“差额报告单”制度,上海钱业的票据清算制度也逐渐完备统一。
除上述庄票的挂失止付和票据清算外,其他一些票据习惯也呈现出不断完善、走向统一的趋势。譬如票据的发行,并非所有钱庄都可以发行票据。早在乾隆年间,“钱商就于上海城隍庙内园,立钱市总公所”{20}(P.401),凡新开的汇划庄在开业前,必须加入钱业总公所,并缴纳会费30两,是谓“入园钱庄”{6}(P.11)。它们享有发行银钱票、签发庄票和汇票的权利,而其他一些未“入园”钱庄,因资本规模较小,钱款收解只能委托汇划庄,不能直接从事票据业务。如此一来,这些汇划庄就将票据发行权操于己手,将丰厚的利润纳入怀中,同时也以其雄厚的资本铸就了票据信用。不仅洋商信任其发出的庄票、汇票,其他内地城市同样通行,甚至在19世纪末形成以“申汇”为核心的商业货款汇兑网络体系{18}(P.107-108)。其他城市虽然与上海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发行票据已成为钱庄、票号、银行的专利,其他商铺无权发行票据,即使发行了,也没有多大信用力。
再如票据的承兑也有着一般通行的“照票”习惯,就是执票人将票据提示给发票之行家,验明其日期、金额等,即加盖印记或签字予以确认。上海还存在庄票和支票承兑责任习惯。“(庄票)如钱庄未倒,自应照付。如钱庄已倒,可将此票退还原付票人,向其另换他票。如原付票人亦已倒闭,则须查明原付票人有无亏欠该庄银两。倘原付票人已为该庄欠户,则此票只能作废。倘原付票人确有银两存在该庄,则此票可留俟该庄清理存款时,照大众办法,一律公摊”。“支票以押脚之商店字号图章为重,故能流通于市;倘商号支出之银洋支票到期不兑,必须向出票之家理直,以杜伪票取巧等弊,准是则应归立票人负责。”{23}(P.550-551)无疑,这些习惯规定是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的。可见,票据承兑习惯在慢慢趋近国际潮流,与近代法律要求渐相契合。
总之,从长时段来看,近代票据习惯在不断走向完善、趋向统一,权利责任区分日益明晰。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由于长期形成的经营观念和方式,以及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延续票据流通的地域界限。因此,即使是有了颁行全国的《票据法》,现实中仍存在众多的区域性票据习惯,一个多元的现实图景乃是不争之事实。
三、票据习惯演进的背后:经济、文化和权力
自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虽由于战争等多种因素影响,近代中国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有兴有衰,但各地的习用票据和票据习惯始终处于稳定发展状态,形成既有信用坚挺、通行全国的“申票”,也有流行一隅的“本埠割条”、“便条”,既有各地均承认的习惯,但也不乏本地习惯的多元局面。是什么力量型塑了这样一种局面呢?
纵观百多年的近代中国票据习惯变迁史,我们会发现其前期的发展可以说是完全自发式的自由发展。也许票据的最先出现并非基于利益而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但随着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人和店铺,以其敏锐的经济意识认识到票据所具有的巨大经济意义,于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票据,健全票据习惯。为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发票人不断完善票据格式、丰富票据种类,票据使用日益普遍,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票据习惯,规范着从票据发行、票据流通、票据承兑,再到票据贴现和清算这样一个完整的行为链。
毋庸置疑,票据习惯的发展演变,是与商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近代票据习惯的历史变迁来看,正是自开埠通商以后,票据习惯才开始有了大发展,可以说,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的扩大,既是票据习惯发展之根源,亦是促进票据习惯发展的催化剂。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边际报酬的递增和实际存在的一个不完全市场起着主导作用。这恰恰映证了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的论断:“有两种力量型塑了制度变迁的路径:报酬递增,以及以明显的交易费用为其特征的不完全市场”{24}(P.130)。从这一点来说,近代中国的票据习惯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并无不同。
然而除上述经济影响因素外,尚有其他因素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票据习惯的演进。首先,票据习惯的发展路径选择还受到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约束及行为人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儒家所秉持的义利观、道德观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和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型塑着商人伦理{25}(P.318-334)。明清之际,人们已经形成“利义之别,亦心而已矣”和“商与士异术而同心”的认识{25}(P.179-182)。但此时期的商人受官僚专制所束缚,并未能突破传统。及至近代,受西潮冲击以及对外商战的需要,商人的历史作用得以凸显,社会地位才得到较大提升,以“经济问题”为核心的心态与生活观亦即“经济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然在中国扎根,道德标准和理性规范也相应调整以适应新财富的生产{26}(P.19-37)。但讲求商业道德的传统并未被丢弃,“信义通商”、“富好行德”始终是商业行为中的基本准则,桑梓造福人、慷慨慈善家、真诚爱国者成为新时期的商人模范形象{27}(P.214-215)。简言之,虽然票据习惯显露出国际化、制度化的发展趋势,但诚信、公义等优良商业文化传统仍影响和规制着商业金融行为,影响着票据习惯的变革。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票据习惯的发展受外力影响颇大,或促进,或阻碍,而随着国家权威日盛,公权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愈大。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票据法》,以规范统一国内票据市场。但由于钱庄等金融机构并未完全现代化,且和银行之间有着利益之争,一些习惯做法仍在实践中得以保留,譬如票据结算,导致上海钱业和银行之间因汇划问题发生多次论争。1935年,因金融风潮,上海钱业被迫同意银钱业集中汇划,所有收解票据均交银行票据交换所轧账{6}(P.522)。1937年,沪战爆发,上海钱业同业公会议决,设立票据交换所,规定会员钱庄福源等46家,每家各派交换员2名到会办理交换事宜,每日下午1时至2时为交换时间{6}(P.541)。此后,银行和钱业的票据交换所虽有合作,但各自为政之时居多。1945年10月,国民党中央财政特派员公署为统一上海银行钱庄票据交换工作,命令银钱两业原有票据交换所合并,所有银行一律参加交换,各行庄间交换余额之划拨结算,集中于中央银行办理{6}(P.542)。至此,上海金融市场的票据结算终归一统。
总之,在中国近代票据习惯的渐进性变迁中,报酬递增与不完全市场型塑着票据习惯的发展路径,然而受二元经济结构所限,中国近代票据习惯很难真正实现一统,最终是在国家行为下才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因此,在明晰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强大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熟人情结、诚信、公义等本土商业文化传统对票据习惯演进的重要影响,更要认识到在“经济主义”兴起之时代,国家公权行为则对票据习惯的最终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结语
在近代一百多年里,票据权力和权利的转移与重组一直在进行,向着统一、完善的趋势缓步前进,而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则体现出明显的依赖性,既依赖传统,又依赖现实。科斯曾指出:“法律体系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清晰的权利界限,使权力能够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进行转移与重新组合。”{28}(P.71)近代中国票据习惯的历史演进恰相吻合。在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初步建成之后,票据习惯也基本完成重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渐归统一,权利属性愈加清晰突出。然而受限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即使在统一的时代大趋势下,近代票据习惯并未真正实现一统,各地仍然存在很多本地票据习惯,构成一副立体的多元的现实图景。
纵观中国近代票据习惯的演进,其早期几乎完全是在市场的推动下发展,后期虽然有政府公权力的介入,但仍保留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说是自由式发展,制度变迁中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6]形成较好的结合。而自清末以来,中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大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法”行为,有着明显的强制性和急功近利特点。两种不同的法律发展路径,孰优孰劣,我们无法做出绝对的评判,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有先验确定的中国法治之路”{29}(P.22)。一百多年的票据习惯变迁史告诉我们,法律的成长途径并非惟一,但惟有源自生活、在实践中成长的法律,其法律的预期和权威才能得以建立,因为“法律是鲜活的生命,而非僵化的规则。”{30}(P.1)中国的法律,必须立基于中国生活。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确立真正的中国法。这才是值得我们珍视和汲取的历史经验!
(责任编辑 晨晖)
【注释】 作者简介:张松,法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17LSB002)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SJB066)的阶段性成果。
[1]票据是一种典型的有价证券,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票据,泛指股票、债券、发票、提单、保单等商业上的有价证券和凭证;狭义的票据则仅指依据《票据法》规定、以支付金钱为目的的特别性质之有价证券,如汇票、本票、支票。本文从狭义言,所论均为金融商业票据。
[2]如李胜渝的“中国近代票据立法探析”,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北洋政府票据立法略论”,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胡旭晟:“20世纪前期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载《湘潭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张群:“北洋时期对票据习惯的调查研究及其与立法的关系”,载《清华法学》2005年第6辑;吕来明和郝维红的“清代票据习惯”,载《中国法学文档》2005年第2期;[日]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牟发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等,以及一些货币史和金融史研究等也有涉及。他们或是规范分析,或是史实介绍,或是票据立法对票据习惯的吸收与摒弃,但对近代票据习惯的演进以及其影响因素却比较忽视。
[3]申票,即上海钱庄开出的汇票,也叫申汇,流通于汉口、天津、青岛、重庆、南昌、宁波、杭州等重要城市,形成申汇买卖进出的市场交易,即申汇市场。各地钱庄都把申汇视为现金筹码。外地钱庄在资金多余时,即在当地申汇市场购入申汇,在资金紧缺时,则售出申汇以回笼资金。可参见马建华、王玉茹:“近代中国国内汇兑市场初探”,载《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
[4]《皇朝经世文编四》卷22。
[5]关于此二条文的诠释比较,参见王敦常:《票据法原理》,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2-58页。
[6]拉坦(V. W.Ruttan)和速水佑次郎(Yuhiro Hayami)等学者认为,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来自四个方面:组织成本、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政治支持。参见V. W.Ruttan,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66,No.5(Dec.,1984) pp.96-145.
【参考文献】 {1}[日]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牟发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俞鸿昌:“清代会票概述”,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4期。
{3}李炘:“我国票据固有习惯之调查”,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法政卷)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4}银行周报社编:《票据法研究(初编)》(二),1922年印行。
{5}黄既明:“汉口钱庄通用票据”,载《银行杂志》1926年第3卷。
{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7}汪宗义、刘宣辑录:“清初京师商号会票”,载《文献》1985年第2期。
{8}陆世仪:“论钱币”,载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第52卷,岳麓书社2004年版。
{9}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艾衲居士:《豆棚闲话?朝奉郎挥金倡霸》,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11}[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鞠方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
{12}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13}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
{14}戴建兵:“浅议清末和民国时期钱庄、银号和银行的票据”,载《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三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15}[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16}[美]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陈潮、陈任译,陈绛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
{18}陈明光:《钱庄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9}戴学文:“清代会票析论”,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4期。
{20}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1}《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22}陈天表:《票据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3}张家镇:《中国商事习惯与商事立法理由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韦森译审,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5}《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6}叶文心:《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王琴、刘润堂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
{27}严昌洪:《在商业革命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8}[美]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9}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0}[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李红勃、李璐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8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