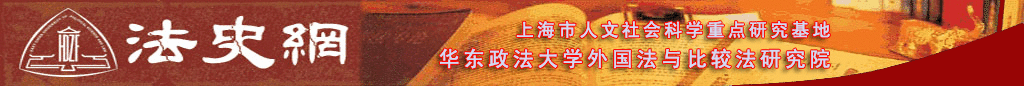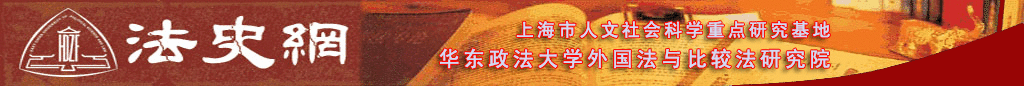内容提要:
“遵用状式”是清代县衙维护地方诉讼秩序的一项基本规定,然而,在诉讼实践中,由于涉讼者贫穷、受衙役搕索、制度改变等因素,“违式”呈状的现象时有发生。既然有制度规定,州县官对“违式”词状当以驳回为要,而事实上牧民之官却多受理此状。两造的违式递呈与县官的准理违式状,究其实质是两者基于地方法规与社会现实的一种博弈。违式递呈展现了清代州县诉讼实态的多重面相,州县官对违式状的不同处理则反映了他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理讼观。
"Compliance with Plaint" was a basic rule by which Yamens of counties maintained the local litigation order in Qing dynasty.Sometimes "Violation of plaint" occurred due to the poverty of the plaintiff,blackmail of the Yamen and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Magistrates of counties should reject the paper of the "Violation of plaint",but they took them for granted.The reason resulted from a game between local statutes and social realities.It showed many facets of suits in states and counties,and different modes of the magistrates reflected their principled and flexible concepts of litigations
关 键 词:
遵用状式/违式/诉讼秩序/理讼观/Compliance with Plaint/Violation of Plaint/Litigation Order/Lawsuit Concept
标题注释:
本文写作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1&ZD093),“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26)的资助。
在清代州县司法中,状是启动诉讼程序的钥匙。诉讼一旦发生,如果两造中的任何一方要请求衙门判决,一般情况下需先到所属州县呈递状词。呈词原则上需有专门的状式,即印有规定格式的诉讼用纸。①但在实际的案例中,“不遵用状式”或“违式”的现象却时有发生。既然地方官府明确规定须遵式用状,两造为何仍违式上呈?县官对这些违式呈状行为持什么样的态度,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司法观念?检讨学界现有的研究,相关成果多侧重于对状式及状式条例的整体思考,而无专题涉及,而事实上对这类“细节”的深描是我们认识传统中国法制的重要依托②。本文拟以清代州县司法档案为主要史料,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官方对“遵用状式”的规定及其内涵
有清一代,中央政府所颁国家法典《大清律例》中对诉讼程序的规范不完备,涉及讼案当事人诉讼行为方面的法律条文更为鲜见。清代地方政府往往会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去规范诉讼程序和两造的诉讼行为,以实现对地方诉讼秩序的有效控制。
(一)官箴书所载的“遵用状式”之规定
对遵用状式的规定,清代的官箴书多有记载。《牧令书》谓:“立状式……受词之大要也”③。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言:“式定则不敢脱……若状式有违,不与准理”,在其所立状式条例中也提到“状不合式……不准”④,“查不合状式者,即批明不合某式,不准”⑤。《纸上经纶》载:“词内务要遵用新版状格纸”⑥。褚瑛在《州县初仕小补》中明确提出“其违式红呈、白禀一概不收”,为何如此,原因在于“盖红呈、白禀既无住址,又无店保,在讼者所费无几,架唆者又易为力。一经接收,则纷纷效尤,以式状之虚设矣。且票传时如匿不到案,差役以无住址、店保藉词推诿,必得饱其所欲而后已。故收红呈、白禀事虽小,而危害甚大,须访明地方情形,即明白晓谕禁止”⑦。《律例指南》称:“请宰州邑者,分别状式二纸刊板,流行一纸照寻常状格无事更张,除人命之外,一切奸盗诈伪诸重情,以及田土婚姻诸细务,总用此格”。⑧《李文襄公别录》曰:“具呈一应民词皆用格眼状式……倘敢不遵状式,仍连写呈状等字样白呈混扰者,除不准外,定行严提重处,决不姑贷”。⑨《海阳纪略》指出:“告词仍遵前颁状式,务要开明道里远近居住都啚,兼写代书姓名……如有奸民不书姓名,以白纸连篇累牍者,概不准理”。⑩《切问斋集·清讼狱禀》言道:“凡有呈词,遵用状式,本属应遵定例”。(11)《覆瓮集》强调:“仰县属人等知悉,今本县刊定状式……有违状式,事涉虚诬者,概不准理。”(12)《政学录》中载:“今定为式,各衙门一体遵行,倘违式滥准,官可知矣……如不合式者,将代书人重责枷号,所告不许准理”,同时列出了24种不同种类的状式。(13)至于遵用状式的重要性,清人潘月山在《未信编》中道出了原委,“告者只需言其紧要,恐字多则易入无情之词,故宜定以字格”,“迨对质之时,颇属虚诞,故颁刻印状,不贵限字,而贵合式”,“如不合式,不与准理,则谎状自少”(14)。
(二)状式条例对“遵用状式”的相关规定
从清代地方司法档案来看,在清代的大多数时间、大多数地区,告状所用正状的状尾部分通常刊有“状式条例”,虽然“率皆自为,风气参差不齐”(15),“各州县自行刊发”(16),但大多要求“遵用状式”,各地呈现出同质性的特征。
以四川省为例。南部县在乾隆年间就规定“不遵格式,叠字重行者,不准”(17);嘉庆年间也有“违式、逾格、双行叠写、字迹潦草者,不准”的呈状限制(18);此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南部县均有“不遵用状式……不准”的诉讼规定(19)。在四川的巴县、冕宁县也有类似的规定,《巴县档案》中状式条例载:“不遵格式……不准”(20),“告无格式……不准”(21)。《冕宁档案》载:“不遵用状式……不准”(22)。《四川叙永直隶军粮府档案》:“不遵用正、副状式……不准”(23)。
川省以外,清代的其他州县也对“告应遵式”在制度上予以约束。如甘肃某县,“不遵状式……不准”(24);浙江龙泉县,“不遵状式……不准”(25);安徽绩溪县,“不遵用正副状式……者,不准”(26);台湾淡水新竹地区,“如不遵式逐一填注,不准”(27);江西宜春县,“不遵颁定状式,及无副状并代书图记,不准”(28);奉天宽甸县,“词状违式者,不准”(29);上海县,“即当恪依定例,按三八呈期,遵用状式赴案控告”。(30)
由上可知,清代地方官府对呈词须遵用状式多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三)“遵式”与“违式”所指何式?
何谓“遵式”?遵什么式?与“遵式”相对的是“违式”,违反什么规定才会被称为“违式”?现择取四川南部县、冕宁县和陕西紫阳县的三种“状式条例”作一分析:
四川南部县
1.将年远并赦前事翻告者,不准。
2.绅衿、妇女无抱告者,不准。
3.词内生员作证者,不准。
4.词内无干证者,不准。
5.词内被告过三人及牵连妇女者,不准。
6.将他事列入词内者,不准。
7.人命不开实在凶手、凶器、在场确证者,不准。
8.盗案失单内不注明银两数目,□件衣服首饰、色样、布疋字号单,棉表□颜色者,不准。
9.不遵格式,叠字重行者,不准。(31)
四川冕宁县
1.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不准。
2.以远年断结之事翻案覆告者,不准。
3.告田土,不粘呈契约者,不准。
4.告婚姻,无媒庚帖、婚书者,不准
5.告吓诈财物,无见证过付者,不准。
6.告出卖田地价足再行率取覆补者,不准。
7.原告过三名者,干证过四名者,不准。
8.以老疾残废之人及妇女作干证者,不准。
9.老人、绅士、妇女具呈无抱告者,不准。
10.不遵用状式、代书戳记,并格内双行叠写,不准。(32)
陕西紫阳县
1.已在前任告准审断,有案不行叙明作何断结者,不准。
2.将赦前及远年旧事翻新告理者,不准。
3.年七十以上,及有残疾并妇女、生监无抱告者,不准。
4.被呈五人以上,干证三人以上,及无故牵连妇女者,不准。
5.生监作干证者,不准。
6.词内只许将冤抑情节据确实书,如粘连欸(款)单、砌人浮词者,不准。
7.无代书戳记者,不准。
8.擅用白呈,不遵格式者,不准。
9.控告赃款,无见证确据及过付者,不准。
10.诉呈续词,不全录前批语者,不准。(33)
从以上三地的状式条例可以看出,衙门对地方诉讼秩序的规定可谓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其中对两造或干证的年龄、人数、呈词内容及书写方式、特殊人群需用抱告等涉讼者的诉讼行为方面都有细致的规定。不难理解,状式条例中的任何一项没有被遵守者都可归为“违式”或“不合式”的范畴。考察各地的司法档案,州县官也有类似的处理意见。如四川巴县,“妇女无抱,着即遵式明白另呈,代书余在沼记责。”(34)四川冕宁县,“词不遵有代书戳记,违式不合,并饬。”(35)云南武定县,“那振祖是否恃强争继,鱼肉愚夷:张国佩等有无助恶苛敛,仰侯差提严讯虚实,并究。该夷年逾七十,并不刊具报(按:应为“抱”字)告,殊属违例,仍即补刊报(抱)告,遵式另呈备案。”(36)浙江黄岩县,“无戳不阅。”(37)广西,“凡呈递状词须具正副二本,……若无副本,则为违式,斥不受理。”(38)
细究上列三地状式条例,我们又不难发现,南部县“不遵格式,叠字重行者,不准”、冕宁县“不遵用状式、代书戳记,并格内双行叠写,不准”、紫阳县“擅用白呈,不遵格式者,不准”的这些规定仅是众多条例中的一条。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不遵式”并不包括条例中所有的规定,而仅仅是指没有使用官方颁印的带有格眼的状格纸。
简而言之,广义上讲,遵守当地关于诉讼的基本规定,特别是状式条例所载的各项规定的诉讼行为都属于“遵式”的范畴。而狭义上的“遵式”仅仅指遵用官方颁印的状格纸。本文是基于狭义上的讨论。
二、诉讼者为何“不遵用状式”
既然官府明确规定,控词须遵式呈递,那么诉讼者为何还“不遵用状式”?通过对《南部档案》所收集到的209件“不遵用状式”案例的梳理与分析,笔者发现其原因复杂多样,其原因有的也互为交叉,为了便于分析,现做如下类型的统计:
(一)经济因素
首先,因家境贫寒,无钱购买状纸。诉讼者为了维护被侵犯的权益而呈请官府解决,但因家境贫穷,无钱购买状纸,不得已而“违式”呈状。光绪十年(1884)八月二十八日,南部县北关外七十岁的乡民王家福称:“民年老家贫,□积赡资囤炭养老”,因“灶户姚庆元向民买炭煎盐,积欠银二百六十八两……分厘不给,害民拆本乏赡,现在举家啼饥号寒,实难聊生”(39),所呈告状没有遵用状纸。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原籍广元县的黄文元,因其妻子逃走,后在“王开寿家得见”,但王开寿“抗不还人”,于是呈词上控。而黄文元的妻子郑氏在三月二十五日逃走时“卷拿衣服钱文”,在“广属旺苍坝开火炮房”为生的黄文元在南部县城内又“举目无亲”,以致“无钱取式,特具红呈”(40)。
类似的原因而致不遵状式的情况也发生在光绪十七年(1891),家住五面山的李长盛因妻子被倒卖而告赵文详等人一案中,李长盛在其违式状纸中称,因其妻子失踪,且“厢柜并开,衣服首饰一搂而空”,后又请人寻访,将钱用完,最后民拌(扮)乞食,挨户找寻”,后在文家坝文双林家找到,但文双林将其殴打不放。李长盛称“惨民人孤势弱,房产当尽,衣服卖完,人财两空”。(41)同年,崇教乡民杨其炳在诉状中直接说:“惨民贫,难遵式”。(42)
其次,遭被告洗劫或勒索,无钱遵式。经济窘困的实际情况可能不如呈词中所说的“日食无度”、“困穷甚极”或“家破人散”那么严重,但遭遇被告的洗劫,对于经济水平普遍低下的清代百姓无异于雪上加霜。
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初一,积上乡孀妇宋氏在状词中称其族人“宋玉连……将民地内豌葫豆麦强割一空,家具器物文约抄拿尽净,尤拉猪牛锁门……民无奈身负冤白,冒喊辕下,无钱取式,特具白呈”(43)。七月十一日,又违式诉言:“去年,玉碧窃人架猪寄托氏家”,反诬宋氏丈夫所窃,“勒搕氏钱三十串,夫妇家贫无出”,便将宋氏一家逐出,并“估罚氏钱二十串,因氏家寒无钱给出”,便“将氏田地五谷稻粮概行获去,又将氏家中猪只器具一空,苦氏全家无有生活,只得乞食长街,鸣冤深望仁天全活母子三人姓名。”(44)
光绪二十八年(1892),积下乡孀妇周廖氏恳称:“家贫如丐无祭,凭族剖分多年有据”,其夫妇“勤俭持家,衣食稍裕”,因“去岁六月,氏夫病故”,族人逼迫周廖氏改嫁,于是周廖氏“暂为另居,搬移出外,佃房栖身”,而族人乘机将其“木料、瓦角及粮食红苕洗掠一空”。于此,周廖氏呈词言:“本应遵式,乃氏家计洗掠殆尽,不已投递白呈,究刁白冤”(45);六日后又违式呈状,称:“氏欲遵式,家计洗掠,赤手无资,不已,投递白呈”(46)。
相对于周廖氏而言,住在王家场的武生徐国藩被洗劫的情况更严重,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二十九日,徐国藩禀称:“徐隆祥等二十余人蜂拥来家,将生紧闭,掳去衣服被罩器具罄尽”,又欲将其妻子李氏谋害,致其“家掳如洗,立站现无,日食难度”(47)。此后,李氏又在告状中称:“无钱遵式,特具白呈”(48)。十月初六日,徐国藩恳称:“伙串抄掳,罄净如洗,困穷甚极,含冤莫告,致生夫妇前迭呈禀,只将身穿衣物尽卖乳子,夫妇目前乏度……惨将生居此店门壁毁尽,量生无钱,难以遵式”。(49)数次呈状都没有遵用状式,而在状词中都提到家中被洗劫一空的情况,可知,突然的变故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是难以承受的打击,以致无法遵式。
类似的案例也发生在光绪二十九年(1893),大竹县民邓炳南“异籍出外操小生理度,确无钱银”,因“财物俱被掠空,人地生疏,无钱遵式,路费又乏”,且“举目无亲”致使无法“措钱遵式”,“情出不己”而数次呈词不遵状式(50)。宣统元年(1908),积下乡孀妇程张氏因讼而致“家破人散”,“在城每日长街求吃度食”,“万般无奈,特写白呈”(51)。
再次,涉讼者遭遇衙役、书差搕索,无钱购买状纸。有清一代,差役持票搕索情况严重,一是名目多,二是去役人多,给两造带来了很大的负担(52),“往往人未到官,资已全罄”(53)。通过对状式的阅读,笔者发现正是这些衙役搕诈勒索,导致一些涉讼者无钱买状。如光绪七年(1881)十月初三,家住宣化乡的赵正贵因“票差将民押店滥食”而致其“一贫如洗,讼费无出”,又加上其父“老病迈弱,食用难度”,“生计莫何”,导致无钱遵用状式(54)。此后,十月十五日的一张违式诉状中,赵正贵也提到“惨民家寒,难受拖累,被差蹭索,坐卧不安”。(55)
光绪十四年(1888),金星乡孀妇在其违式状词中说:“陈洪、余顺藉票欺民女流,恶搕差费,私押滥食。三月初一,氏恳省累,沐批遵式,差等乘机赴府□□勒和,恶搕民出钱八千四百文,无给,又不送审,起意缠累,氏贫帮工,实难受害”。(56)同样,光绪十六年(1890),汪正寿的违式诉状中说:“书差来到,民家下无奈毫无钱银应付书差”。(57)这张状词中虽然未明确提出被书差搕索情事,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类情况。
此类例因在清代地方诉讼中多有发生。针对本文的研究,在搜集到的209件“不遵用状式”案例中,因经济因素致使“不遵状式”的案件有119件,占总体比例的57%之多,它至少给我们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面相,经济因素是诉讼者是否或者能否“遵用状式”的一个基本支撑点。
(二)时间因素
首先,讼案日久,讼费开销大,乏钱取式。案件的审判时间越长,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就会越高,最终导致涉讼者无钱购买状纸。如光绪年间的一桩钱债案件,积上乡民张东平“以估撇赖还炭银等情具告周宗敏一案”。此案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二十九日始,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仍未完案。以至于张东平其后屡次违式呈词言:“日食俱废”(58);“可恶联武……势大欺民懦讷,兼乘伊病,图延日时……已具呈七张,口岸累深,银案两悬”(59);“拖延逾限日久,分厘抗偿,害民停贸,官经两任,讼累年余,羁城静候口岸费深,银案两悬”(60);“民遭伊撇骗讼累两年余,官经三任,费资若干,生易(意)倒塌,乏钱取式,只得再具白呈”(61)。同样,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十三日,家住在离城九十里的金兴乡民徐应成,呈词言:“羁城候案日久,口案深重,乏钱开销”,而致投递词状没有“遵用状式”(62)。
其次,事由仓猝,缮呈不及,告状时间紧迫,“不遵用状式”。一些迫不得已,又急于维护自己权益的告状者,为了尽快让纠纷得到解决,也会在呈状时“不遵用状式”。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初七日,家住离城一百四十里的永丰乡民李朝,因其堂弟李安在光绪十二年(1886)当掉他用以“自耕作膳”的两块桑地,又复当与别人,并在四月初六日将李朝殴伤,致使李朝“寅夜奔辕喊冤”,在四月初七就将词状上呈县衙,并祈说“赏补白呈”(63)。
(三)“不遵用状式”成为一种诉讼策略
笔及至此,我们不禁会问,涉讼者真的穷得或被敲诈得连一张状纸钱都买不起吗?细细推敲,我们不难发现,上述所叙除有一部分是实情外,“不遵用状式”成了一种希望博得县官受理词讼的诉讼策略。
首先,涉讼者夸大案情,以博取审判者的同情和重视。为了让所呈词状得到州县官的受理,告状者往往会夸大或虚造陈词,把自己描述得贫困无比非常可怜,或以贫穷为借口,或借故案情重大,来博取审判者的同情和重视。诉讼者在呈词中所提及的贫穷、被洗劫、被搕索等原因,不一定完全情真,只不过是一种诉讼策略。
为了突出自己的悲悯朴实,而把对方叙说得恶贯满盈,以使案情复杂化,使得州县官的关注点不在其是否遵式之上,而在于“辨别良莠,讯夺案情”上;或者说相对于案情的本身,是否遵式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光绪二十八年(1902),积下乡孀妇周廖氏状告周建子一案。周廖氏先说自己“孀守十六岁独子日夜攻读,不敢怠倦”。而对周建子却述为“不守卧碑,仗衿为势,惯于在乡寻风捕影,遇事搜搕善良,受害者莫可如何”。随后又言周建子“欺氏寡子,起意谋□”,“纵支其姑母周马氏出头,无凭无据栽诬氏与人不苟”,趁周廖氏在城候案未归,周建子又串掠其家财物。周廖氏凭族周人清等理论被斥还。又恐吓称要将周廖氏“同子及雇工均各除毙方休”。(64)此类言辞会对州县官造成一些影响,认为此为“良”,而彼为“恶”。这样即使周廖氏所呈是“违式”的状,县官也会给予同情,予以受理。
其次,涉讼者“徒告不图审”的诉讼心理也使得他们没有觉得“遵用状式”是一种必须。清末的一份《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就提到,徒告不审,希图拖累,乃川省一大弊病。(65)徒告不图审者有的是给对方施压,以便在上衙门之前解决争端。(66)仅仅呈状上诉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把官司打完,或仅以这种方式吓唬对方,达到自己的目的。(67)而有的纯粹是破坏对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其目的并不在于解决纠纷或者结案,而是以图拖累。如在宣统元年(1908),新镇坝民湛国海违式呈状,县官批词“违式不阅”之后,湛国海即没有再次呈词(68)。一些诉讼者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觉得没有必要在“遵用状式”上去较真,而是蜻蜓点水式的,递上一状就不了了之了。一旦有这样的动机,一些涉讼者为达到自己的“零付出”,当然也不会花费去购买状式了。
三、州县官对“不遵用状式”的态度
按照官府的制度规定,所有“不遵状式”的呈词都应被驳回,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却多有出入。依笔者的统计,州县官对此类“违式”案件的批词主要有“违式不阅”、“违式另呈”和“不遵式特饬”三种。第一种批词可以理解为“不准”,第二种“违式另呈”说明遵式上呈后还有受理的可能,可理解为“半准”,第三种则是对违式之状直接性的受理。州县官为何要“(半)准”这类“不遵用状式”的呈词?
(一)州县官认为案情比较严重,有审理的必要
在处理重情案件时,州县官不会简单地只放在涉讼者是否遵用状式的层面上。作为清代所设的最低一级行政单位,维持地方治安是州县官的基本职责之一。遇至细故案件,州县官还可依照衙门所设状式条例给以不予受理的理由,或委托家族组织或乡保组织负责化解,如“所呈果否不虚,仰该处保甲等迅查明获夺”,而一旦遇到重情案件,为了避免因调节不当而酿制后祸,或担心因案件牵连到自身,州县官往往会在批词中批以“违式特饬”或“不遵式特饬”的慎重处理。
对于州县官来说,重情案件发生后,诉讼者是否遵用状式的重要性远不及对重案的解决本身。因为州县官可能会因此受到处罚。《大清律例》中规定:“凡告谋反、叛逆,官司不即受理,差人掩捕者,虽不失事,杖一百,徒三年。因不受理掩捕以致聚众作乱,或攻陷城池及劫掠人民者,官坐斩监候。若告恶逆,如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之类,不受理者,杖一百。告杀人及强盗不受理者,杖八十……违者,随所告事理轻重,以坐其罪”(69)。因此,州县官也担心错过实在冤情,曾位居湖南巡抚的陆燿于其著《切问斋集》中言:“呈控者且不遵用格式,代书戳记,每以白头纸状混行呈控,在上司衙门惟恐其中或有实在冤情,随时准受”,为了避免因不准状式而错过冤情或重情案件,陆燿还建议,“本属应遵定例,今遇白头纸状一体准收,既启小民侥幸尝试之心,益滋奸徒刀笔之弊,合无仰恳宪台通饬阖省大小衙门,除叛逆重情并命盗大案,实有屈抑者,其词状随时准受,不拘格式”(70)。
光绪三十年(1904),南部县政教乡民孙建基具告孙联芳通匪殃民抢业反诬一案,涉讼者的几次呈词都没有使用正规的官颁状式,而从数次批词可以看出州县官对案件本身的重视程度远超过涉讼者是否遵用状式。如:“是否省释,本县自由权衡,毋庸率渎”、“候讯明究办”、“案经委员会审拟办,毋庸率渎”、“尔案业经严办,前获各犯并未供及孙元善等行贿情事,毋得率渎,违式特斥”(71)。发生在光绪三十年(1904)的一起命案也能证明这一点,金兴乡民夏周氏具告周邦文霸业将夫逼毙阻葬勒搕一案,县官批词曰:“仰原差即将两造来案候覆讯,毋延,违式特饬”(72)。而这些呈词都没有遵用状式。
(二)特定时期的制度所限
首先,官代书裁撤后,作状“不必拘定格式”。清代官府为了防范讼师刁唆词讼,创设了官代书制度(73),把作状人的身份由民间转向官方。诉讼者如欲告状,必须由官代书代为书写状纸,并加盖官代书戳记,所呈状纸才能生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官代书制度也弊象横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川总督赵尔丰认为:“代书虽为例设,然积久弊生,择肥噬瘦,勒索呈费,实与讼师无异”,于是下令裁撤官代书(74)。最后,四川南部县知县史久龙便“禁笔代书”,于六月初一日“将代书一律裁撤”(75)。官代书裁撤之后,多数告状者无法作词呈状,赵尔丰便责令南部县收呈时“不必拘定格式”(76),从而使得这一阶段“不遵状式”呈状的情况明显增加。从《南部档案》来看,史久龙在任时,对官代书裁撤之后的一段时间,诉讼者基本没有“遵用状式”,实为裁撤官代书之故。
其次,状格纸的字数限制不能让双造尽叙案情。清代各地所用的状格纸对呈词字数进行了限定,这种规范因有固定的状格字数,可以避免因“不限定字格,枝词蔓语,反滋缠绕”而带致的困扰(77)。从《南部档案》来看,官府审呈基本遵守这一规定。然而,这种规定也有其不适用性。如遇事实过多,却非依限定字数实能说明。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一件违式状词,告状人李凤鸣、李凤翼呈词言:“本应遵式,又奈情长,难以叙清,民特投具白呈”。批词为“案据李祝氏具呈已经批示,凭理据呈,是否情真,既据称迭理难息,两造、干证□已来城,候随堂提质讯夺”(78)。对于这种规则与实际迥异的状况,《广西调查诉讼习惯报告书》中对此进行解释,认为此“系相对的限制,非绝对的限制”(79),只要非故意为之,某些不符合个别规定的呈词不见得州县官会必然不准,而是酌情予以受理。
(三)州县官的怜悯之心
对部分诉讼者所持有的怜悯心也会影响州县官是否受理违式状。对于鳏寡孤独年岁老迈的诉讼者,生计本就难以保障,若权益又再遭侵害,州县官并不会对此置若罔闻。即便诉讼者所呈状没有遵用状式,对百姓的怜悯之心也会使被称作牧民之官的州县官受理违式状。
如光绪十年(1884),王加福告姚庆元欠银不还行凶殴伤一案,因光绪七年(1881)姚庆元向其买炭煎盐积欠二百七十八两,导致王加福举家“啼饥号寒,实难聊生”。而王加福已年逾七十,以□积赡资囤炭养老。姚庆元又欠其数量巨大的债款,这使年老家贫的王加福难以聊生。当王去向姚讨要债款时,姚却“仗刁估撇、抓民行凶”,将王加福及其妻与子打伤,州县官批词:“估准唤案一讯”。(80)对于这样年已古稀,又遭撇殴的诉讼者,之于对“遵式”的规定,州县官此时更愿施之同情,同时审讯此案冤实真假。
(四)拦舆呈状或县官新任
相对于到诉讼程序复杂且门规林立的衙门递呈,在州县官外出时拦舆呈递是一件十分危险但又相对便捷的做法。州县官针对这些情况有时也会表现出为民作主以肃冤情的示范。
光绪二十八年(1902),王洪宝具告王昭德等串谋霸吞搕逼兄命一案,王洪宝因其家业良田十余亩被同姓不宗的王昭德强逼“将绝业卖与民兄洪举,以便搕钱瓜分”,并于“今三月,伊等强逼祖母同至兄家,逼勒立契”,其兄不允。而王昭德等“意在夺业分肥,因先示威以夺兄气,即将兄毒殴周身青紫伤鳞几毙”。因王昭德等“重贿房班”,致王洪宝“迭控不理”。“今逢宫保大人荣升过境,量必起死人而肉白骨,民不拦途喊叩?况恶等忿民控究,每每搕索不休,家业殆尽,有死无生,泣血奔叩总督部堂大人行辕,赏准伸冤作主施行”。(81)此后王洪斌也告称“洪举受凌无已,情急自缢身死”。此两件告状显然没有用正规状式,但“部堂大人”受理了此案,批词言:“尔兄王洪举如被王昭德等威逼自缢,既迭控县,何致任听书役贿销,殊难平信,仰南部县速行查案,据实录覆核夺,控词人命切勿餙欺,致有冤抑,是为至要,词发仍缴”。(82)这种拦舆告状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州县官为何会准理违式状的另外一种面相。
县官新任时为树立威信或建立一地父母官形象,也会对违式案件给予受理。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部县政教乡马治政因纠党阻耕逆殴等情具告马文相一案。马治政告称,马文相趁秋种时“纠党阻耕”,同年十月初五又将马治政殴伤。“今逢仁天下车,特以红呈,叩赏作主”。县官宝震批词为:“着即来案候当堂验伤核夺”。(83)
(五)衙门的生存利益链所致
一个诉讼案件,从写状、递呈到最终的堂谕出来,在各地均有一套程序。沿着这个思路,我们还会发现,“不遵用状式”的状纸由于有官代书、歇家、各房衙役、幕友等关口的把持,在理论上是进不了衙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在哪里?除了上述的讨论外,更在于衙门内部的生存链。只要有官司入衙门,他们就可能获得更多的陋规收入或非法收入,岂能放过?
四、结论
通过对本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反映了清代地方社会诉讼场域复杂性与多样性
清代地方社会的诉讼场域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征。就本文所论,讼者确因贫穷导致无钱购买状纸的情况与以贫穷为借口而不遵用状式的诉讼策略往往交织在一起;州县官企图通过“遵用状式”的规定来达到规范地方秩序的正当诉求与他们通过售卖官颁状式以获得经济利益的背后私利性动机相互掺杂;地方政府对法律秩序的理想构建与地方社会的实际困境(如所属衙役、幕友等群体因生存而导致的搕诈行为)相冲突。
(二)反映了州县官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理讼理念
客观而言,状式条例对维护地方社会的诉讼秩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让涉案者明了讼案始终的阶段性程序规定。事实上,县官在判案时对于违式呈状予以驳回的比例远高于受理的情况,这体现出州县官维护帝国基层司法秩序的原则性一面。
然而,若完全严格遵守规定,在处理数量巨大且种类繁杂的诉讼事务时,其办法则显得有失弹性。对部分不遵用状式的诉讼完全拒绝,有可能激发民怨,甚至导致失控。这样一来,不仅无助于维护地方秩序的稳定,县官的考绩与晋升也会受到影响,再加上一些州县官多有同情与恻隐之心,所以,为了尽快调解纠纷,平息事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州县官对一部分“不遵用状式”的诉讼予以受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作者简介:
吴佩林,西华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吴冬,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会理州于光绪二十五年(1901)六月初四的一则告示就载:“民间一切词讼,务须遵用状式,不得用红、白纸缮呈”。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②参见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中华书局2013版;付春杨:《权利之救济:清代民事诉讼程序探微》,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邓建鹏:《清朝〈状式条例〉研究》,载《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邓建鹏:《讼师秘本与清代诉状的风格——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李艳君:《从“状式条例”看清代对书状的要求》,载《保定学院学报》2008第3期;胡谦:《从黄岩诉讼档案看清代州县讼案诉状格式》,载《兰台世界》2009年第4期下半月;江兆涛:《清代诉状制度研究》。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③(清)王植:《受词》,载(清)徐栋辑:《牧令书》卷十八,道光戌申秋刻。
④(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刑名部一·词讼·立状式》,濂溪书屋刊本。
⑤(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词讼·批阅》,濂溪书屋刊本。
⑥(清)吴宏:《纸上经纶》卷五,《词讼条约》,转引自郭成伟、田涛整理《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⑦(清)褚瑛:《州县初仕小补》卷上,《违式呈词不收》,载《官箴书集成》第八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743页。
⑧(清)凌铭麟:《律例指南》卷十二,《论人命》,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⑨(清)李之芳、李钟麟编:《李文襄公别录》卷五,《申严反坐禁止白呈》,清康熙刻本。
⑩(清)廖腾煃:《海阳纪略》下卷,《告词条规示》,清康熙浴云楼刻本。
(11)(清)陆燿撰:《切问斋集》卷十二,《清讼狱禀》,清乾隆五十七年晖吉堂刻本。
(12)(清)张我观:《覆瓮集》卷一,《版设状式等事》,清雍正四年刻本。
(13)(清)郑端撰:《政学录》卷五,《状式》,清光绪刻畿辅丛书本,载《官箴书集成》第二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341-343页。
(14)(清)潘月山:《未信编》卷三,《准状》,陆地舟刻版,载《官箴书集成》第三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73页。
(15)《法部等会奏京师各级审判由部试办诉讼状纸折并单》,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第1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86页。
(16)(清)石孟函辑:《广西调查诉讼习惯报告书》第三章第一节,广西官书局排印,清宣统二年。
(17)《南部档案》2-61-2-D43,乾隆十三年九月廿三日。
(18)《南部档案》3-82-1-D1178,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19)《南部档案》4-124-D1122,道光六年;《南部档案》6-201-1,同治七年十一月廿三日;《南部档案》7-106-D157,光绪元年四月十七日。
(20)《巴县档案》6-1-1793,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21)《巴县档案》6-2-1697,嘉庆十一年五月廿一日。
(22)《冕宁档案》,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23)《四川叙永直隶军粮府档案》1-648-1,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24)转引自杨泽荣:《清代司法审判情况的缩影——甘肃省档案馆新近征集的清代诉讼档案阅析》,《档案》2004年第5期。
(25)《龙泉档案》M3-1-4519,宣统二年五月一十八日;M3-1-2862,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2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27)《淡新档案》33205-1,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
(28)光绪十六年四月。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刘诗古博士提供此材料。
(29)《宽甸县公署》,光绪二十九年。转引自张勤:《中国近代民事司法变革研究——以奉天省为省》,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3页。
(30)《上海县示(为禁用白禀事)》,载《申报》第11913号,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九日,第17版。
(31)《南部档案》2-61-2-D43,乾隆十三年九月廿三日;2-61-1-G12,乾隆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32)《冕宁档案》,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33)《紫阳档案》,同治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感谢陕西师范大学高学强教授提供此资料)
(34)《巴县档案》6-4-2559,咸丰三年八月十三日。
(35)《冕宁档案》,咸丰六年三月初四日。
(36)“李夏系诉为私法难当,呼天急救事”,嘉庆十八年十月初三日。载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编:《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37)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38)(清)石孟函辑:《广西调查诉讼习惯报告书》,广西官书局排印,清宣统二年。
(39)《南部档案》8-956-1-D586,光绪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40)《南部档案》10-59-1-D778,光绪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41)《南部档案》11-63-2-D680,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42)《南部档案》11-73-6-D789,光绪十七年七月月十一日。
(43)《南部档案》11-40-2-D379,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一日。
(44)《南部档案》11-40-6-D383,光绪十七年七月十一日。
(45)《南部档案》15-767-3-D151,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
(46)《南部档案》15-767-4-D152,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
(47)《南部档案》18-276-2-D1386,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48)《南部档案》18-276-4-D1388,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49)《南部档案》18-276-5-D1389,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六。
(50)《南部档案》16-164-8-D799,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51)《南部档案》23-68-1-D447,宣统元年二月。
(52)吴佩林、蔡东洲:《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的差票考释》,载《文献》2008年第4期。
(53)(清)汪辉祖:《学治说赘·堂签簿》,同治十年慎间堂刻汪龙庄先生遗书本。
(54)《南部档案》8-387-3-D141,光绪七年十月初三日。
(55)《南部档案》8-387-5-D143,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
(56)《南部档案》10-55-4-D744,光绪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57)《南部档案》10-345-7-D1093,光绪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58)《南部档案》15-769-11-D195,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三十。
(59)《南部档案》15-769-12-D196,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60)《南部档案》15-769-20-D208,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61)《南部档案》15-769-31-D224,日期不详。
(62)《南部档案》15-739-6-D1353,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63)《南部档案》13-128-3-D1368,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七日。
(64)《南部档案》15-767-5-D153,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65)李光珠辑:《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藏。
(66)吴佩林:《清代地方民事纠纷何以闹上衙门》,载《史林》2010年第4期。
(67)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160页。
(68)《南部档案》20-536-1-D720,宣统元年十一月。
(69)《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诉讼·告状不受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3页。
(70)(清)陆燿撰:《切问斋集》卷十二,《清讼狱禀》,清乾隆五十七年晖吉堂刻本。
(71)《南部档案》16-711-19-D875,光绪三十年三月九日。
(72)《南部档案》16-688-8-D470,光绪三十年十月一日。
(73)吴佩林:《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的清代官代书研究》,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
(74)《四川官报》光绪三十四年,第十八册,第2页。
(75)《南部档案》18-639-4-D1281,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76)《四川官报》光绪三十四年,第二十八册,第6页。
(77)(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刑名部一·词讼·立状式》,濂溪书屋藏版。
(78)《南部档案》18-933-2-D1384,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四日。
(79)(清)石孟函辑:《广西调查诉讼习惯报告书》,广西官方书局排印,宣统二年。
(80)《南部档案》8-956-1-D586,光绪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81)《南部档案》15-764-1-D109,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
(82)《南部档案》15-764-1-D112~D113,光绪二十八年。
(83)《南部档案》17-660-1-D1326,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