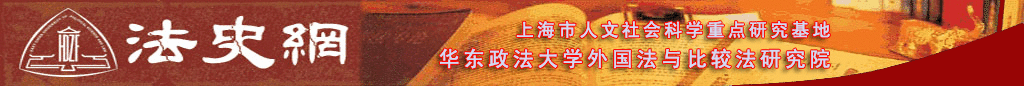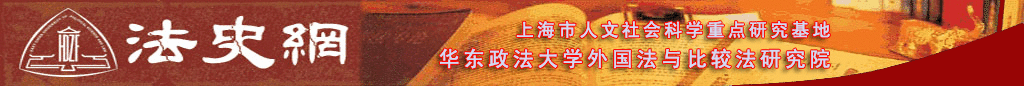内容提要:
衡平法在数世纪的发展变迁中,“良心”始终是一条主线,进而形成了所谓的衡平法“良心”司法传统。沿着“良心”这一主线,审视不同时代法官们在行使衡平司法管辖权及适用衡平规则时的不同风格,藉此观摩衡平司法传统的发展路径。在对衡平法“良心”司法传统的摸索中,认为衡平法面临被普通法“融合”浪潮而依然无法被彻底替代的原因,即在于这衡平法产生之源起、历经若干世纪的若隐若现、却依然贯穿衡平法始终的“良心”。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Equity throughout these centuries,conscience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running-through theme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so-called Conscience-based judicial tradition in the equitable jurisdiction.This Article examines,tracing along the theme of conscience,various styles and approaches adopted by generations of judges when they were exercising their equitable jurisdiction and applying the rules of Equity,so as to mark the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judicial tradition.It concludes that it is conscience as administered by judges,no matter in a visible or invisible way,that has made Equity irreplaceable and unabsorbable under the impending wave of fusion of the Common Law and Equity.
关 键 词:
衡平/良心/衡平司法传统/衡平法与普通法的融合/equity/conscience/equitable judicial tradition/fusion of the common law and equity
作为一种代表着公正、公道之司法理念的“衡平”(Equity),并不为英格兰法律体制所独有,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在罗马法、教会法中,均可看到它的身影[1];然而,作为一套客观存在的法律规则体系——衡平法,作为一种可单独区分的司法管辖权——衡平管辖权,却是地道的英格兰法律史的产物。一如梅特兰(Maitland F.W.)所言:从历史的角度对衡平法下定义,是他所能想到最好的方法①。然而,对衡平法的了解如若仅停留于将其视为一套规则及一种司法管辖权,则未免忽略了这一独特法律现象之实质特性:将英格兰衡平法与亚里士多德之衡平观念及罗马法中的衡平概念区分开来的,不是外在的衡平规则与衡平管辖权,而是其内在的“良心”基因——一种针对被告人之良心而延展的法律现象。本文的写作目的,即在于沿着历史的线索,摸索衡平司法传统的“良心”主线。
衡平法基于“良心”的司法传统,在数世纪的变迁中亦展现着不同的面貌,“良心”的色调在不同时代大法官的手中,或明或暗:那些“衡平热烈拥护者”(equity enthusiasts),强调自然法意义上的良心,着重衡平法的灵活性与柔韧性,在广阔的空间内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而那些“衡平怀疑论者”(equity sceptics),则强调规则意义上的良心(或者甚至否认衡平法的良心特质),严格遵循先例,认为不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仅因衡平之故就赋予一项衡平权利或施以衡平救济②。然而,不论一代又一代的大法官们对良心在衡平司法中的地位或高举或贬抑,良心始终是一条主线,进而形成了所谓的衡平法“良心”司法传统。
德沃金(Dworkin R.)曾将判例法比喻为一本“连载小说”,每位法官都在其前任的基础上,延续着故事的叙述③。判例法学者几乎一致认为,英格兰法律根植于“记忆之外”的远古惯例。亦如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所述:“司法实践并不来自书本。法官所承袭的是传统,深埋于共同记忆的传统。”④这些昔日先贤的司法智慧,构成“这一行当的集体判断”[2],为承继者奠定基础并划下无形的边界。正如卡多佐所描述的那样,司法传统那“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像大气一样时刻压迫着我们,哪怕我们意识不到其重量。”[3]
本文欲沿着“良心”这一主线,在对衡平法的“良心”管辖权作简要溯源后,审视不同时代法官们在行使衡平司法管辖权及适用衡平规则时的不同风格,藉此观摩衡平司法传统的发展路径。依照年代,拟将近、现代衡平司法风格分为五个时期:(1)17世纪以前“良心裁判”盛行的年代;(2)17至19世纪衡平司法中“良心”的规则化;(3)20世纪司法舞台上的保守派、开拓派与理性务实派为衡平司法带来的多元化风格;(4)世纪之交司法界出现的回归衡平法本原与重塑“良心”基石的“复古”潮流;(5)20世纪司法变革中的“宾汉法庭”及英国最高法院展现的衡平司法风格。有鉴于国内业已存在较多有关衡平法早期发展的论述[4],本文将重点对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以后的近、现代衡平司法风格作一巡礼。
一、衡平法的“良心”管辖权溯源
衡平法之所以以“良心”为基石,衡平法院之所以被称为“良心法院”,衡平管辖权之所以被视为一种“良心”管辖权,均源自英格兰法律史中一个特定事实——国王的“凌驾性剩余司法权”⑤。提到国王权力,不得不从《大宪章》(Magna Carta)谈起。
在1215年《大宪章》颁布之前,英格兰中央集权的王室法院已然形成,即坐落于威斯敏斯特的普通民事诉讼法庭、王座法庭及财税法庭。这些代表王室司法管辖权的普通法法庭,从其13世纪的形成到19世纪下半叶的司法组织改革前,除部分改革外,在本质上少有变化。在王室法院已然创立的情况下,似乎可以认为,国王已经用尽了他的司法权力⑥。随着《大宪章》有关“法律的正当程序”这一观念(即不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深入人心⑦,在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统治下的14世纪中叶,确立了一些制定法,意图对王室再度设立新的司法管辖权作出限制⑧。因而,“法律的正当程序”中的“法律”,指的仅是王室法院中实施的普通法,即本王国的法律。
然而,在英格兰的传统与习惯法中,国王乃“正义之源”,国王的主权(包括司法权)并没有因《大宪章》这一限制而殆尽。从国王加冕与宣誓的传统与习惯中,可以看到国王在王国的地位。先来看被视为诺曼征服后历代国王宣誓模板的无备者艾塞尔雷德(Ethelred the Unready)国王的宣誓,其中有关司法的部分是:“保证判决公正和仁慈,公正和仁慈的上帝将以他永远的仁德宽恕我们。”[5]到了爱德华二世(Edward II),其誓词以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问答方式进行。大主教问:“陛下,您能本着仁慈审慎之心客观地运用权力并在判决中实现公平和正义吗?”国王回答:“是的,我能。”[5]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的誓词与其前任基本一致⑨。可见历代英格兰国王均宣誓以“公正”(justice)与“仁慈”(mercy)行使司法权。因而,如果常规的法律运作未能达致公平与正义,为不公平与非正义提供救济,则成为国王责无旁贷的职责,故国王拥有常规司法管辖权之外的用以施行正义之“凌驾性剩余司法权”⑩。
上述《大宪章》“法律的正当程序”条款与国王的“凌驾性剩余司法权”,为日后衡平法发展的若干特征提供了历史渊源上的解释:(1)《大宪章》将国王的剩余司法权的行使,局限在现行法律的施行未能达致公平与正义的情况下,并且不触及“法律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生命、自由与财产”。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衡平法在日后的发展道路中,不涉及刑事法律,亦极少涉及侵权法律领域,而是主要集中在商事法与家庭法领域(11)。(2)这也解释了为何衡平法并不是作为与普通法相竞争、相矛盾的一套法律规则而出现,相反,衡平规则是普通法的补充与矫正,只有当普通法因规则的刚性而缺少回旋余地时,衡平法将其适用“柔化”,力图将法律适用的结果导向公平与正义。(3)国王凌驾于常规法律体系之外的司法权,决定了代表国王的衡平法官具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申诉人所寻求的,是出自国王恩典的一种救济(a remedy as of grace)(12),既是恩典,则不属申诉人应得的权利,而是仰赖于国王(或代表国王的大法官)是否决定给予这样的救济。向大法官提出的申诉书,亦常以祈求的语气,恳请国王视乎上帝的慈爱,以仁慈的方式给予救济(13)。因而,迄今,法官依然对是否施以衡平法上的救济拥有高度自由裁量权,并且,寻求衡平法救济之人,必须“手洁心清”(14),即自身没有可谴责之处,否则,不具备请求国王施行怜悯的资格(15)。由此可见,衡平法的“良心”管辖权首先源自国王的良心,经由国王良心的保管者大法官实施,以纠正被申诉人违背良心的行为。
二、17世纪以前的衡平司法风格:“良心裁判”盛行的年代
由前文对衡平法历史的追溯可见,衡平司法管辖权的源头在于国王的良心,大法官作为国王良心的保管人,使得衡平法院成为“良心法院”。在衡平判决尚未系统而规律地进入判例汇编时,情况确实如此。16世纪50年代后,尽管零星出现了一些衡平法的判例汇编,如1557年的《凯里》(Cary)、《狄更斯》(Dickens)和《托费尔》(Tothill)等判例汇编,但系统的汇编至17世纪尚形成,尤其是17世纪后期的诺丁汉勋爵时期。因而,17世纪以前的大法官,基本不受先例的约束,而主要依照良心作出裁判。
埃利斯密尔勋爵(Lord Ellesmere)于1596年至1617年间担任大法官,可被视为横跨16与17世纪的大法官,同时亦为现代衡平法的奠基人之一。从他的经典判例“牛津伯爵案”(Earl of Oxford's case)中(16),可以管窥那个“良心裁判”盛行年代的衡平司法传统。埃利斯密尔勋爵的判词,全篇围绕着“良心”展开,且在通篇判词中,“衡平与良心”或“良心与衡平”作为衡平法的代称反复出现,且两个词的首字母均为大写,这意味着在当时的大法官眼中,衡平即为良心,良心即为衡平。埃利斯密尔勋爵强调,因着人的良心的败坏,产生了衡平法院良心管辖权的需要;而衡平法院所做的与唯一可能做的,乃是厘正被告人的良心,原告人获得的也是出于良心的救济(17)。同时,在这份判决中也未显示出任何普通法与衡平法之间的“敌对”关系(18);相反,埃利斯密尔勋爵认为普通法与衡平法应当“携手”矫正法律适用中的极端与严苛情形(19)。
由这一经典判决的逻辑和理由可知:迟至17世纪初,衡平法惯以良心为基本内涵,大法官也惯以良心为圭臬断案(20)。这印证了福特斯鸠爵士(Sir Fortescue)在1452年的一宗衡平法案件中,为回击一项基于普通法提出的辩护理由而作出的回应:“我们在这里谈的是良心,而非法律。”(21)
三、从诺丁汉勋爵到埃尔登勋爵:16至19世纪“良心”的规则化
17世纪(尤其在后叶)系统而稳定的衡平法判例汇编萌动,是导致衡平法“凝固”为如普通法般之法律规则的直接原因,由此亦使得衡平法的判案基准“良心”趋向规则化。在衡平法院与普通法院合并前的三个世纪的历程中,三位衡平大法官对衡平法的形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分别是:自1673年至1682年任职的诺丁汉勋爵(Lord Nottingham)、自1737年至1756年任职的哈德威克勋爵(Lord Hardwicke)、以及于1801年与1807年两度担任大法官并任职二十年之久的埃尔登勋爵(Lord Eldon),他们分别成为衡平法在这三个世纪发展中的标志人物。
(一)诺丁汉勋爵时代:从“自然与内在的良心”到“法律与政策上的良心”
诺丁汉勋爵被誉为“现代衡平法之父”。他的另一个称呼是“芬奇爵士”(Sir Finch H.),故此,他在任时的衡平法判例汇编称为《芬奇》(Finch)(1673年-1680年),为纪念其名而编纂的衡平判例汇编称为《芬奇判例汇编》(Finch's Precedents)(1689年至1722年)。诺丁汉勋爵对衡平法至高的贡献,是他通过判决,将散乱的衡平规则,经过含义的厘清与规则的梳理,整合为一套得以与普通法并行且和谐相处的法律体系。霍兹沃斯(Holdsworth W.)如此描绘诺丁汉勋爵:“他的判决表明他具备一位伟大法官应具之全部特质。他对复杂案情的分析与把握是如此娴熟,不但鞭辟入里,还泾渭分明。他可以对一项原则及由该原则衍生出的理由作清晰而逻辑分明的剖析;这一能力使得他能够对不同的法律原则作出精确地判辨,由此清晰划定各自的适用范围。”(22)以出版英格兰法律经典为使命的塞尔登协会(Selden Society),在1954年与1962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诺丁汉勋爵衡平判例集》(Lord Nottingham's Chancery Reports,Vol.1&2),以此彰显诺丁汉勋爵对衡平法规则系统化与规则化所作的贡献(23)。
鉴于此,诺丁汉勋爵视“良心”在衡平管辖权中的地位与意义,有别于他的衡平法先辈,他的著名论断是:“对于那‘源于自然与内在’(naturalis et interna)的良心,非本法庭所需要考虑的;我断案所依照的,仅仅是‘法律与政策上’(civilis et politica)的良心,并依附于确定的规则;对公众而言,一项完全秘而不宣的信托、担保或协议,否定其法律效力,远远要强于仅仅因为大法官的个人喜好及想象而使当事人丧失财产。”(24)这表明,诺丁汉勋爵所理解的“良心”,已经与埃利斯密尔勋爵甚至更早期的时代大不相同,前者所指是法律与规则上的概念,而后者则属于宗教、道德或哲学层面的含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诺丁汉勋爵在将衡平法规则化与系统化的过程中,亦将“良心”从道德与哲学领域,“降格”至规则的层面。然而,整体而言,此时的衡平法正迈向确定性,衡平规则的形体愈加清利,同时其与生俱来的灵活性与创造力亦如日方中。
自1682年诺丁汉勋爵卸任至1737年哈德威克勋爵上任期间,有两部著作见证了衡平法在这半个世纪期间内的发展程度。第一部著作是1727年出版的由法兰西斯(Francis R.)编订的《衡平法谚》(Maxims of Equity)(25),其中记载的十四条衡平法谚语,后世的规则除对其作出个别修改与限制,基本没有本质上的改易。法律谚语的出现,表明衡平法除在判例汇编中有迹可循外,其基本原则亦已成型,借助法律谚语的形式表达出来。另一部标杆性著作是1737年由巴洛(Ballow)撰写并匿名出版的《衡平法专论》(A Treatise of Equity)(26)。依据霍兹沃斯的描述,在衡平法发展史上是承上启下之作,它以衡平法在法律制度中存在的必要性为基础,历陈衡平法业已发展成熟的逐项规则,如依照衡平法取得财产的方式、在不具备充分对价情形中执行合约的方式等,并且在确定规则的前提下,依然保留着衡平规则灵活适用的空间(27)。这种有章可循下的适度柔韧有余,实际上亦代表了当时衡平司法权之行使特色。
(二)哈德威克勋爵时代:衡平法“形塑期”的完成
哈德威克勋爵担任衡平法院大法官的二十年(1737年至1756年),再度见证了继诺丁汉勋爵后衡平法发展的又一黄金时期。哈德威克勋爵在诺丁汉勋爵对衡平法规则化的基础上,使它们得以最终成型。
18世纪是商事法律蓬勃的世纪,在普通法方面,被誉为“商法之父”的曼斯菲尔德勋爵为普通法商事法律原则奠定了基础;与其并肩而行的,是另一边厢的哈德威克勋爵,他们同时面对18世纪新的商业环境、新的财产处置方式以及所要求的对新型产权认可与救济的需要。在哈德威克勋爵主掌衡平法院的年代,衡平产权(相对于普通法上的产权)之性质与特征已确定,有关知情原则(doctrine of notice)的一些规则亦已发展成熟,未支付对价者(volunteer)与已支付对价之买受人(purchaser for value)在衡平法中的不同地位已然明晰。另外,与遗嘱及财产授予契据(settlements)等相关的法律问题,催生了诸如清偿(satisfaction)、撤销遗赠(ademption)、地产选择权(election)及转化(conversion)等衡平法规则与救济方式(28)。
可以认为,在哈德威克勋爵时期,衡平法主项主要规则均已成型。哈德威克勋爵另一难得之处是,他能够因时因地把握衡平规则的确定性与灵活性。一方面,他遵照已确立的规则行事,但另一方面又不认为应当对规则盲从。因而,他在处理有关欺诈和各种迅时应变措施(sharp practices)的案件中,行使宽泛的司法自由裁量权(29)。
(三)埃尔登勋爵时代:衡平法从规则化到僵化
哈德威克勋爵用他二十年的大法官生涯,完成了衡平法的形塑期,而埃尔登勋爵则用另一个二十年,将其前任的形塑工程加以完善与修缮。埃尔登勋爵曾两度担任大法官(自1801年至1806年,再自1807年至1827年),对衡平法在19世纪最初三十年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克里(Kerly)在其19世纪末出版的《衡平法的历史》(History of Equity)一书中,如此评断埃尔登勋爵对衡平法发展的影响:“在埃尔登勋爵退休之时,衡平法已经不再是一种矫正普通法的规则体系,我们只可能将其描述为由衡平法院实施的‘救济正义’(remedial justice)的一个组成部分。”(30)
霍兹沃斯在《英格兰法的塑造者》一书中,详列了埃尔登勋爵对衡平法规则的主要贡献:在“艾莉森诉艾莉森案”中(31),埃尔登勋爵阐释了法庭在何种情形下会为未支付对价之人(volunteer)提供协助;在“达特莫夫伯爵案”中(32),他阐释了在与递耗财产(wasting property)与归复财产(reversionary property)相关的信托案件中受托人的义务;在“阿尔德里奇诉库珀案”中(33),他阐释了确定债务人财产清偿次序(marshalling doctrine)的相关规则;在“默雷诉埃利邦克案”中(34),他阐释了妻子在财产授予契据(settlements)所享有的衡平权利,这是《已婚妇女财产法》通过前对这个问题至为重要的阐述;在“布莱斯诉斯托基斯案”中(35),他确立了受托人对合作受托人(co-trustee)在违反信托时的责任(36)。通过衡平判例这精细的雕琢过程,埃尔登勋爵无疑将衡平法塑造得更为规则与细致,而这亦正体现了他所认为的衡平法的发展方向。他有一段广为引用的陈述,流露了他精心将衡平法规则化的目的:“这间法院(即衡平法院)所发展出的法律原则,应当与订立确定规则的普通法那样,被稳定地确立,且统一适用,当然,它们应当被小心谨慎地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中。有人说这间法院确立的法律原则是随着每一任大法官的转换而改易的,我完全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当我离任之时,如果忆起我曾做过什么事情为‘衡平法随大法官的脚而变’这样的论断提供过任何的理据,将没有什么会比这使我更难过。”(37)
埃尔登勋爵倾其毕生之力,将所谓的“秩序”与“可预见性”引入衡平法,并以此主导着衡平法在19世纪甚至是20世纪的发展方向。到19世纪末期,时任上诉法院民事庭庭长的杰赛尔勋爵(Lord Jessel M.R.)在1878年的一份判决中,毫不掩饰地对衡平法的发展状态作出这样的评论:“这间法院(即衡平法院),正如我常说的,并不是一间‘良心法院’(Court of Conscience),而是一间‘法律法院’(Court of Law),意思是,衡平法院亦与普通法院无异地受着法律原则与先例的约束。”(38)可以说,自诺丁汉勋爵以降的衡平法规则化潮流,发展至19世纪末,已俨然成了另一套普通法,名曰之“良心法院”亦遭受否定。
于20世纪中期登上英格兰造法舞台的丹宁勋爵(Lord Denning)对这个时代的衡平法作此总结:“在诺丁汉勋爵与哈德威克勋爵时代,衡平法拥有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但到了埃尔登勋爵手中,则变得呆板而僵化,并且自此一直是这样。”(39)丹宁勋爵显然对埃尔登勋爵将衡平法的规则化推至极致,甚至导致衡平法如普通法般僵化,甚为不满。哈佛大学的庞德教授于1905年发表的《衡平法的衰落》(The Decadence of Equity)一文中,亦表达了对衡平法未来的担忧(40)。他看到在过去的19世纪,完全是规则化法律的世纪。在维多利亚时代(自1837年至1901年),随着英国商业与工业的蓬勃,对法律的要求更多地是确定与清晰,商业社会需要规则与秩序多于因法官自由裁量而带来的灵活与不确定(41)。庞德在20世纪初即感叹,“具有生命力之衡平法(a living equity)的时代已逝。”(42)
埃尔登勋爵的观念与做法尽管代表了当时的主流,但即使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依然能够听到坚持衡平法院为“良心法院”这样的声音。见证过1875年司法改革这一历史时刻的时任大法官赛尔邦勋爵(Lord Selborne),在1883年的一个案件中,坚持称衡平管辖权为“良心管辖权”:“英格兰的衡平法院从来都是良心法院,针对被申诉人本人,而非针对财物;而在行使这种针对个人的管辖权时,衡平法院一直惯于强制履行并不在他们管辖权内的合同与信托关系中涉及的事物。”(43)这样的声音尽管纤芥,但却表明衡平法的“良心基因”依然未被规则化的浪潮泯灭。
四、20世纪的保守派、开拓派与理性务实派
在20世纪,至少在司法管辖权上,已无普通法与衡平法之分。于1875年生效的《司法组织法》(Judicature Acts 1873-1875)为英格兰司法体制带来重大变革,普通法法院与衡平法院被合并于统一的高等法院。但这一“融合”并未触及两套法律体系在实体规则层面各自的领域,两者“合”而不同。埃叙伯纳(Ashburner W.)对此有一著名比喻:“这两股清流,尽管流淌于同一管道中,却并排前行,水流互不混淆。”(44)往昔的衡平大法官,已转身成为了上议院的议长,其作为衡平法官的标志性身份已然消失。但作为司法机构的最高长官,大法官对法律发展状态与方向的把握,其重大影响如故。
(一)20世纪前半叶:浓重的保守气氛与划时代的“唐纳修判例”
20世纪前半叶的大法官们,大多属于保守型,如于1895至1905年间出任大法官的哈尔斯伯雷勋爵(Lord Halsbury),他被认为“不属于最伟大的普通法法官”,他甚至“不是法学家或法律学者,对作为一种体系的法律不抱有浓厚的兴趣。”[6]然而,著名的31卷本《哈尔斯伯雷英格兰法》(Halsbury's Laws of England)(1907-1917)却因他担任1907年第一版的总编辑而命名。另一位同样“对法律原理兴趣不大”[6],并两度出任大法官的是海尔善勋爵(Lord Hailsham)。
然而,看似“沉闷”的20世纪前期,却产生了普通法历史上的划时代判决、奠定了现代侵权法基础的“唐纳修诉史蒂芬森案”(Donoghue v.Stevenson)(下简称“唐纳修案”)(45)。该案的终审判词,如同一个微缩的舞台,又似一次历史性的“投票”,昭示了当时“保守派”与“开拓派”两种法律思维的碰撞,后者的“险胜”造就了这一划时代的判例。其中代表“保守派”的,是巴克马斯特勋爵(Lord Buckmaster),他令人瞩目的贡献,在商事法尤其是公司法领域,如有关公司独立法人资格的“玛考拉诉北方保险公司案”(Macaura v.Northern Assurance Ltd)(46)以及在枢密院所作的针对董事不得篡取公司商业机会之义务的“库克诉迪克斯案”(Cook v.Deeks)(47),其中对董事在衡平法上所负的受托人义务有着精辟的阐释。不过“唐纳修案”,却透现出他固守先例的一面。
“唐纳修案”提出的,从狭义上讲,是有关产品责任的问题,即生产商是否应对与其无合约关系的消费者负注意义务;从广义上讲,则与最根本的侵权责任相关,即在何种情境下,过错人须向与其无合约关系的受害人负注意义务。当时的法律是,若过错人与受害人之间没有合约关系,则前者无需向后者承担责任。“唐纳修案”中的法官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应当突破合约关系的限制,将责任延伸至没有合约关系的双方。巴克马斯特勋爵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没有必要与足够的理由将此责任延伸,他对当时没有恪守先例的两个判例提出批评(48),认为它们“最好是被稳固地埋葬,以免它们那不安分的幽灵常常跑出来混淆视听。”(49)与其同席的另一位英格兰法官汤姆林勋爵(Lord Tomlin)对巴克马斯特勋爵的意见表达了赞同,从而构成了该案中的异议判词。埃特金勋爵(Lord Atkin)和来自苏格兰的芬克顿勋爵(Lord Thankerton)及麦克米兰勋爵(Lord Macmillan)构成了该案的主流判词,结果以“三比二”的多数,造就了“唐纳修”判例。埃特金勋爵借用《圣经·新约》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50),确立了“邻舍原则”(Neighbourhood Principle),将侵权法律责任比喻为行为人对其“法律上的邻舍”之责任,前者对后者负有注意义务(51)。
(二)20世纪中期:“打破旧习者”丹宁勋爵带来的衡平新风
在丹宁勋爵开始踏上英格兰法律舞台的20世纪中期,大法官之职主要由“保守派”法官履任,如于1940年至1945年任职的西蒙子爵(Viscount Simon),以及于1951年至1954年任职的西蒙斯勋爵(Lord Simonds),丹宁与两位大法官(及同时代的某些同袍)在司法风格以及对某些法律问题的认知上,相差甚远,他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中期的两股塑造法律的力量。
西蒙斯勋爵以严格遵循先例而闻名,在他参与的有关信托的案件中,他均严格依照字义解释相关文件,常常仅出于文件纂写方式的缺陷即否认信托关系的存在(52)。这种做法不禁让人想起当年普通法因僵化而陷入的困境,反而给予了衡平法成长的空间,如今,衡平法在某些拘谨而僵化的司法风格下,亦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如果说西蒙斯勋爵的做法较为极端,那么同时代的某些重要法官则属于“温和保守派”,他们在面对衡平法之规则度与自由度的问题上,主要倾向于前者。例如丹宁的两位前任:于1937年至1949年担任上诉法院民事庭庭长的格林勋爵(Lord Greene M.R.)和于1949年至1962年担任此职的埃瓦舍勋爵(Lord Evershed M.R.)。格林勋爵在1948年的“有关迪普洛克遗产案”(Re Diplock)中,表达了他对衡平司法的基本观点:“若主张衡平法上的权利,应当首先证明该权利在历史中及在衡平法院的实践与先例中曾出现。倘若仅仅出于需要在当前案件中施行‘正义’,而我们就毅然破天荒地实施这一管辖权,这是不足够的。”(53)埃瓦舍勋爵则在1954年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所作的一次题为《对普通法与衡平法融合七十五年后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usion of Law and Equity after 75 Years)的演讲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衡平司法管辖权所代表的那种“棕树下的正义”之警惕。在谈到衡平法应当施行公正时,他说:“当然,事实的真相是,在文明社会中,司法应当依照已确立的规则进行,而不应当存在例外。不管你认为法官们有何等优秀,倘若每一位法官仅依照他自己所认为的正义去断案,那么社会将陷入极大的困境与高度的不确定性。”(54)同时,他还表达了对“棘手案件造就恶法”(Hard cases make bad law)这一说法的认同,认为法官不应当仅因为规则的适用在某一或某类案件中将造成不公正而偏离该规则,因为在某一案件中的公正,或许会对另外一百个案件带来不公正。埃瓦舍勋爵总结道:“不完美的人类社会或许会在特定的场合作出一些不公正的判决,但这也是为了保全人类更大的益处。”(55)
在这个对先例与法律的确定性顶礼膜拜的时代,丹宁勋爵以“打破旧习者”(iconoclast)自居,通过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打碎或意图打碎在普通法中久已树立的“偶像”(56)。因着衡平管辖权的频繁行使,丹宁勋爵亦被视为“一名纯粹的衡平法官”(a pure equity judge)(57)。丹宁勋爵在1952年于伦敦大学学院作的题为《时代呼唤新的衡平》(The Need for a New Equity)的演讲中(58),发出了与上述主流观点不同的声音。丹宁勋爵所言之“新的时代”,既指二战之后的时代,亦指自1952年开启的伊丽莎白时代(a new Elizabethan era)。他如此描述这种时代对法律的要求与期待:“新的时代为人们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亦赋予他们新的眼界。随着这些变化,产生了对新的法律规则的需求,以维持新的秩序,回应新的思维。”(59)丹宁勋爵认为,法律对时代需要的回应,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第一是拟制,第二是衡平,第三是立法。他的重点是针对衡平。在该演讲中,丹宁勋爵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当时衡平司法之僵化的深度失望,他列举了当代三个较为瞩目的衡平判例:1944年上议院的“迪普洛克案”(Re Diplock)(60)、1951年王座分庭的“汤普森诉尔斐案”(Thompson v.Earthy)(61)以及1952年上诉法院的“阿姆斯德朗诉斯德恩案”(Armstrong v.Strain)(62)。丹宁勋爵以法院在这三个案件中的做法为例,批评法官们将衡平法推至无以复加的僵化境地,并感叹现代的法官与二百年前那些伟大的衡平法官是如此地不同(63)。丹宁勋爵以此总结该次演讲:“我再次重申:我们到哪儿去寻找这种新的衡平呢?不是在法官中寻找,因他们无权立法。也不在上议院中寻找,因他们依然受自己错误的约束,或更准确地说,是受自己先例的约束,即使这些先例早已过时。我想,应该在我们大学里依然活跃的新生代中寻找。”(64)丹宁勋爵的总结,既表达了对老旧思维的失望,又寄望于新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新的法律界接班人。
(三)20世纪中后期的理性务实派:一种“渐进式”的衡平司法风格
与丹宁勋爵担任上诉法院民事庭庭长二十年(自1964至1982年)的几乎同一时期,上议院亦出现了几位对现代普通法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律勋爵,他们是雷德勋爵(Lord Reid)、厄普约翰勋爵(Lord Upjohn)、威尔伯福斯勋爵(Lord Wilberforce)及迪普洛克勋爵(Lord Diplock)。如果说丹宁勋爵在其司法生涯的前期(即成为民事庭庭长之前)主要是与西蒙子爵与西蒙斯勋爵所代表的极端保守派的交锋,那么在其后二十年的司法生涯中,则主要与这股代表着理性与务实精神的法律勋爵们交手。
有数个经典的回合值得在此一述。第一个回合,有关弃妻衡平。这是丹宁勋爵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在1952年的“本戴尔诉麦克维特案”(Bendall v.McWhirter)中终于确立(65),并苦心经营了十余年的一项衡平规则。而在1965年的“国家教省银行诉爱恩思沃夫案”(National Provincial Bank Ltd v.Ainsworth)中(66),以厄普约翰勋爵与威尔伯福斯勋爵作出主要判决的上议院,彻底否定了弃妻衡平权利的存在。第二个回合,也是在家庭法领域,即丹宁勋爵在1955年的“柯布诉柯布案”(Cobb v.Cobb)中(67),确立了“家庭资产”(family assets)这一衡平法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家庭财产的分割。而上议院(主审法官包括雷德勋爵、厄普约翰勋爵与迪普洛克勋爵)在1970年的“佩蒂诉佩蒂案”(Pettitt v.Pettitt)中(68),再度否定了丹宁勋爵建立的“家庭资产”概念(69)。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丹宁勋爵另一项建树——根本性违约原则。丹宁勋爵最早在1956年的一个案件中确立(70),后被上议院于1967年推翻(71);但丹宁在1970年的“哈伯兹案”(Harbutt's "Plasticine" v.Wayne Tank and Pump)中再度将其成形(72),但依旧被上议院于1980年推翻(73),其中威尔伯福斯勋爵与迪普洛克勋爵坚定地表达了对在合约中引入这一原则的反对意见。
上述法律勋爵们对丹宁勋爵衡平司法中创新实践的否定,并不代表他们属于保守派或是盲目遵循先例者,相反,他们或许属于对规则与灵活性平衡有度的法官。他们否定丹宁勋爵创设的某些新的衡平权利,如弃妻衡平或家庭资产等概念与权利,并不表明他们对衡平管辖权的否定。威尔伯福斯勋爵在著名的有关公司清盘的“爱博拉希米案”(Ebrahimi v.Westbourne Galleries Ltd)中(74),有着对衡平的精彩论断,并由此奠定了公司法中两项重要衡平规则(即以“正当且衡平”(just and equitable)为由将公司清盘原则,和以遭受“不合理损害”为由要求给予救济的规则)的实施基础。威尔伯福斯勋爵在该案中以衡平法的视野看待公司这一商业实体:“这些字眼(即“正当且衡平”)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有限责任公司不仅是一个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在这个法律实体的背后或其中,存在着个人实体,他们附带着权利、期许与相互间的责任而存在于公司之中,这一切并不必然被淹没于公司的架构中,而公司法总是留有一定的空间对这些权利、期许与责任作出认可。”(75)正是出于对存在于公司这一独立法人实体中的个人实体之“权利、期许与责任”的认可,当这些“柔性”权利被侵犯或期许被摧毁时,衡平法将给予救济。威尔伯福斯勋爵继续说道:“正如衡平法通常所做的那样,‘正当且衡平’这一理由使得法院可以将法律权利的行使置于衡平考量因素(equitable considerations)之下,这些考量因素产生自组成公司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在这种特定的个人关系中,某法律权利的行使,或是其行使的特定方式,将引致非正义与非衡平的后果。”(76)因而,衡平法将介入,干预该法律权利的行使,以避免该“非正义与非衡平”的结果。此乃公司法赋予小股东的有力救济方式之一——“不合理损害救济”(unfair prejudice remedy)——的法理基础(77)。
总体而言,与丹宁勋爵同时代的、对战后普通法及衡平法的发展与走向起着重要影响的雷德勋爵、厄普约翰勋爵、威尔伯福斯勋爵及迪普洛克勋爵等——有人将此时期称为“雷德与威尔伯福斯时代”(The Reid and Wilberforce Era)(78),他们并不如前辈们那样保守而盲目地因循先例,但在行使衡平管辖权时又不会被标签为“棕树下的正义”,他们为衡平法的主观部分注入了理性的成分,他们对偏离先例或是创造先例的情形,都处以适度的谨慎,并以渐进、递增的方式(incrementally),发展普通法,从而造就了这一稳定而又富有创造力的法律发展时期。
五、世纪之交:回归衡平法本原与重塑“良心”基石?
20世纪的最后十年,似乎见证了丹宁勋爵在1952年有关“新的衡平”的演讲中寄语新生代产生的新思维。这种新的衡平司法风格在信托法领域表现得较为明显,新一代的法官似乎已不再严格地奉传统法律规则为圭臬,他们更愿将信托视为人们可以利用的一种处置财产以达致不同目的的工具。当代衡平法学者哈德森教授(Hudson,A.)形容两代法官对法律的不同态度,就如同两代人对音乐的不同品味一般,新生代(在此主要指1990年代登上法律舞台的法官们)不再为法律本身的缘故而遵循法律,似乎只要人们处理财产的方式不违反根本性原则,将尽可能赋予其法律效力(79)。
在此世纪之交,一个特别的现象是,当法律学者(包括某些法官)在为是否应当将普通法与衡平法完全在实体上融合争论不休时,衡平法最独特和本源的基因——“良心”——一再地现身这个时期法院的判决中。自埃尔登勋爵勋爵将衡平法的规则化推至极致以来,当杰赛尔勋爵于1878年宣布衡平法院(这里指法院的衡平管辖权)已不再是“良心法院”,而是“法律法院”时(80),一个世纪以来,法官们(不论是保守派、理性派还是开拓派)或多或少已对“良心”一词隐而不提。因而,当20世纪末分别担任上议院首席大法官的戈夫勋爵(Lord Goff)与其继任人布朗尼·威尔金森勋爵(Lord Browne-Wilkinson)(81),在某些“情”与“理”不得双全的判决中,回归几个世纪前为衡平法勾勒出最初框架的衡平法谚,回到“良心”这一起始点,重述“良心”作为衡平规则与衡平管辖权的基础地位,人们不禁发问:法官们是否是在重塑“良心”的基石呢?衡平司法传统,是否出现了“复古”潮流——即使不是回到埃利斯密尔时代,至少也是回到讲究规则但又备具生产力的诺丁汉勋爵与哈德威克勋爵时代呢?
(一)戈夫勋爵:回复衡平法本原
先看戈夫勋爵是如何回归衡平法最初之使命的。在戈夫勋爵的若干重要判例中,尤其是他偏离主流观点而作出的异议判词,他似乎意图尽可能地从最广义的程度上实现司法正义,典型的例子可见于他在1994年的“婷斯里诉米莉根案”(Tinsley v.Milligan)(82)、1995年的“怀特诉琼斯案”(White v.Jones)(83)、及1996年的“艾斯灵顿案”(Westdeutsche Bank v.Islington L.B.C.)中的判词(84)。
在第一个案件中,戈夫勋爵拒绝认可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在共同投资之房屋中的衡平产权,理由是她与另一方当事人在购房的安排上出于骗取福利的违法动机,基于衡平法的“净手原则”(Clean Hands Rule)(此亦为通行了二百余年的衡平法谚之一),戈夫勋爵拒绝为其提供衡平法上的救济。而在第二个案件中,戈夫勋爵是出于“提供一种实际可行的正义(practical justice)之冲动”(85),而判决案中存在职业疏忽的事务律师,应当对因其疏忽而未能从遗产中受益的当事人承担责任,他强调,如果法庭对这种损害未能“量身定做”出合适的救济方式,以填补法律空缺,则将导致重大的非正义(86)。而在第三个案件中,戈夫勋爵再次回到最初的衡平法谚:“衡平法不允许无救济之权利”,再次回到衡平法产生之初的使命,即在普通法救济不足够时,补足该救济,以达致正义之解决方式。他为法院依然因诉讼形式的缘由而拒绝提供衡平法上的救济,如此感叹道:“我实在难以相信,在20世纪末的今天,我们的法律竟然还会因诉讼形式的束缚而裹足不前。”(87)戈夫勋爵在判词的结尾处,呼吁让法律得以实行“完全正义”(full justice):“种子已经埋下了,只是其生长被局限于狭小的空间内。方今,我们应当允许它在这个全新的法律领域(即有关恢复原状的法律)自然地伸展枝丫。并不需要施行基因改造工程,只需司法创新那喧暖的阳光,散发出宜人的光芒即可,而不是躲在厚重的历史云层下。”(88)
上述例子标示了戈夫勋爵的司法思维与风格,他乐将判决建基于衡平法最根本的原则,如衡平法谚中的原则,并鼓励司法创新,认为法官(尤其是拥有终审权的上议院法官)不应自缚手脚。因而,戈夫勋爵被形容为“老派的衡平法官”(old-fashioned equity lawyer)(89)。
(二)布朗尼·威尔金森勋爵:重申“良心”在衡平规则体系的核心地位
与戈夫勋爵同一时期的布朗尼·威尔金森勋爵,当他在“艾斯灵顿案”案中称“‘良心’一直是且依然是整个信托制度最为根本且毫无争议的基础”之时(90),其效果如同一声响雷,划破自埃尔登勋爵以来长达两个世纪累积的历史云层,再次声言“良心”在信托法的核心地位。在这个衡平法已几乎被等同于信托法的年代,这样的申张无疑重又唤醒人们对衡平法与生俱来之道德内核的意识。然而,不能因此就将布朗尼·威尔金森勋爵归为与丹宁及戈夫勋爵同伍的“纯粹的”或“老派的”衡平法官。他的衡平司法风格与戈夫勋爵不尽相同,而这种对比又是显而易见的,因他们二人常在重要的判例中同席,而两人又对衡平法的重要问题持不同意见。
典型示例即为上文引述的三个判例:1994年的“婷斯里诉米莉根案”、1995年的“怀特诉琼斯案”、及1996年的“艾斯灵顿案”。在第一和第三个案件中,布朗尼·威尔金森勋爵与戈夫勋爵持不同意见,前者并未如后者般对衡平法中的道德因素给予过多的垂注,而是从务实的角度判断是否应当认可当事人衡平法上的产权。而在第二个案件,即“怀特诉琼斯案”中,尽管布朗尼·威尔金森勋爵与戈夫勋爵在该案中达成了一致判决,但两者却是践行着不同的路径。如前所述,戈夫勋爵是依从传统的“道德高度”,出于施行正义的“冲动”(91),出于为损害提供救济的初衷,而将行为人的责任建立于“正义”、“救济”等传统衡平法哲学与考量因素的基础上的,采取的是一种“法哲学路径”(jurisprudential approach)。而布朗尼·威尔金森勋爵却恰恰相反,他采取的是判例法中经典而稳妥的“务实路径”(practical approach),在根本法律原则下,通过与已确立责任类别的类比,从而演绎出新的责任类别(92)。
在上述经典场境中,布朗尼·威尔金森勋爵展现出更接近威尔伯福斯勋爵的司法风格。哈德森教授对他的评价是:他并非一位“头脑混乱不清的道德主义者”(woolly-minded moralist),而是一位在先例中谨慎游走并适度有为的“务实主义者”(pragmatist)(93)。
六、21世纪的司法变革与衡平法面临的“一统化”危机
21世纪见证了英国司法体制的另一次重大改革。于2005年通过的《宪法改革法》(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取消了上议院作为最高司法机构的职能,并于2009年10月1日设立新的英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故此,2009年犹如一百三十年前的1875年,成为英国法律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年份。
(一)“宾汉法庭”与英国最高法院
上议院历史上最后一任首席大法官,是于2000年6月接任布朗尼·威尔金森勋爵、并于2008年9月(即最高法院成立前夕)退休的宾汉勋爵(Lord Bingham),他在司掌“末代”上议院的九年间,承前启后,以适度的“谨慎与雄心”塑造法律规则(94),使得英国司法体制在经历巨大变革的情境中,得以平稳过渡。因而有学者称此九年间的上议院为“宾汉法庭”(The Bingham Court),盛赞其判决“显著地清晰而进取”,并寓意此为法律变革时代的一个重要时期(95)。“宾汉时代”法律界最热门的话题是司法独立,这也成为最终于2009年设立最高法院、将法律勋爵们从立法机构上议院中分离的导源。宾汉勋爵及其同袍——来自南非的斯汀勋爵(Lord Steyn)成为当时最为活跃的倡导完全司法独立的推手,后者愈发直接将矛头指向已在英国历史上延续一千四百年的大法官一职(96)。
单论司法风格,“宾汉时代”见证了法官的更新换代。2004年1月,发生了法官人事最大规模的换届,在司法风格上偏向保守路线的三位法律勋爵——哈顿勋爵(Lord Hutton)、霍伯豪斯勋爵(Lord Hobhouse)及米勒勋爵(Lord Millett)——同时退休,其职位由三位新晋法律勋爵取代,其中最为耀眼者,就是英国史上第一位女法律勋爵——黑尔男爵夫人(Baroness Hale,Lady Hale),她亦于2009年成为首批最高法院法官。黑尔男爵夫人执锤于英国的最高审判机构,无疑为英国法律氛围注入一股新鲜的空气,学者们用“新的思维”来刻画她带来的这股新的空气,尤其在涉及女性权利、儿童权益及精神健康等方面(97),黑尔男爵夫人通过众多异议判词,申明她与其男性同袍不同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大多获得法律界的好评。黑尔男爵夫人的衡平司法风格主要体现在有关家庭房产权益的案件中,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几个里程碑的判决中,她均与另一位著名的、且被标签为“衡平法出身”的法官——沃克勋爵(Lord Walker)——作出联席判决。
沃克勋爵于2002年担任上议院常任上诉法官,并与黑尔男爵夫人一道,于2009年成为首批最高法院法官。标示着沃克勋爵衡平思维的典型判例,是他在晋升为法律勋爵前夕在上诉法院审理的“珍宁斯诉莱斯案”(Jennings v.Rice)(98)。该案涉及财产权益禁反悔原则,法官需要确定与损害比例相应的赔偿金额。时任上诉法官的沃克,和布朗尼·威尔金森勋爵在1996年的“艾斯灵顿案”中重申信托制度的“良心”基础一样,亦将财产权益禁反悔原则奠基于“良心”。他如此解释这一衡平原则的机理:“该衡平权益并非仅来自申诉人的期待,而是产生自他的期待、因信赖而蒙受的损害以及若允许捐赠人反悔则将导致的‘对良心的违背’(unconscionableness)等的结合。”(99)沃克上诉法官重申:“财产权益禁反悔原则之实质,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避免‘违背良心’之结果。”(100)只是,这样的“良心基准”并没有得到坚持,在较为新近的判决中,“良心”一词已不复见于沃克勋爵所处理的类似的判决(101)。
在家庭财产法领域,沃克勋爵与黑尔男爵夫人在有关婚姻关系(及准婚姻关系)下的房产的衡平产权的案件中的处理方式,亦备受争议甚至是诟病。典型的案件见2007年的“斯达克诉道登案”(Stack v.Dowden)(102)及2012年的“琼斯诉柯诺案”(Jones v.Kernott)(103)。在前案中,涉及一对同居者对共同购置房产的权益,该房产置于女方名下;在后案中,同样涉及一对同居未婚者,但该房产由双方以联名共有的方式享有。沃克勋爵与黑尔男爵夫人在两案中悉作出了联合判决,对独有产权与联合产权给以不同处理:对前者,他们视其为推定信托(constructive trust),当事人享有之份额取决于其共同意愿;而对后者,他们视其为归复信托(resulting trust),当事人之份额取决于各自在金钱上的投入(104)。这种对家庭(及准家庭)财产权益的不同处理方式,遭到了来自学界的批评,有些认为这种处理方式给相关法律领域带来的是“困惑”而非“条理化”(105);有些则直言要求最高法院能对家庭房产的归属与份额订立一套“统一规则”(106)。总而言之,新一代的最高法官们似乎在衡平法的主要领域尚未交出令人称道的答卷。
(二)衡平法的未来:将普通法与衡平法“一统化”?
梅特兰在其1909年出版的《衡平法》讲义中曾“预言”:“这一天将会到来,当那日,律师们不会再问这条法律规则是衡平法规则还是普通法规则:只要知道这是一条由高等法院稳定适用的法律已足够。”(107)这一天是否已经到来了呢?程序上已经合一的普通法与衡平法,是否需要(或者已经)在实体规则中再度“融合”呢?对此,英格兰法律界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1.“融合论”:将衡平法与普通法在实体规则上合一
这种声音,以牛津大学的波克斯(Birks P.)教授及沃芬顿(Worthington S.)教授为代表,他们极力主张将衡平法彻底融入普通法规则,形成一套统一的法律规则。
以波克斯教授为代表的牛津学派将私法依照触发法律后果的“事件”与法律将作出的“回应”,将私法分为四大类:同意、误行、不当得利及其他事件,继而将法官在特定类别案件中可行使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局限于该类别事件所允许的范围内(108)。这种所谓的“分类学”(taxonomy)在法律界的反响热烈。哈德森教授认为,牛津学派所意图达致的“秩序”,并不是和平社会中人们可以预见法律将作何回应的那种秩序,而是一种将可能引发权利与义务的各种情形以类似法典的方式将其置入一套复杂的图表中,然后机械地依据所属的权利义务类别,决定可能获得的救济(109)。因而哈德森教授称其为“巴士时刻表”,将法律简化为毫无哲学可言的规条(110)。
当代衡平法权威著作《施奈尔论衡平》(Snell's Equity)亦对此作出了类似回应,认为这是法律的“删减主义”(reductionism),删减的结果将导致法律“过于简化”,使得某些法律或衡平权利之间的特征与界限变得模糊不清(111)。而这种“删减主义”对衡平法的影响是致命的,因其在实质上否定了衡平法作为区别于普通法之法律规则的存在。例如,许多衡平规则游离于这些分类的边缘,无法将其切实地归入任何一类,典型的例子为允诺禁反悔原则(112)。另外,《施奈尔论衡平》指出,衡平法基于“良心”之内在本性(亦即对违背良心行为的回应)对达致实质正义具有不可替代之作用,这是上述牛津学派将权利与义务简单分为几种类别的体制所取代不了的,因而,“假定法律权利及其相应救济仅可通过一套单一、排他的分类而获得,这完全是错误的,并且也必然是过于简化的。”(113)剑桥大学的维戈(Virgo G.)教授所针对的倒并非这种分类学上的做法,而是认为如果分类的话,将直接触发衡平法之“回应”的“违背良心的行为”(unconscionable events)应被单列为一类“事件”,而与其他类别并举(114)。
由上述英格兰主流衡平法学者的回应可见,牛津学派主张的“分类法”并不是最适合判例法体系的法律处理方式,法律的发展从判例法系的角度看来,应当是因社会与商业实践的需要而循序渐进,发展路径乃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
沃芬顿教授的出发点与前述以波克斯教授为代表的牛津学派相一致,即让两套并行的法律规则在实体上融合,并使得法律规则更为统一及一致。她的做法不是备受争议的“分类法”,而是更为直接地将衡平规则并入普通法规则,最终出现梅特兰所预言的“不分彼此”。但沃芬顿教授对普通法与衡平法之关系的看法与梅特兰有着根本的不同,她并不认为二者相处和谐,亦不认为衡平法的适用是为了促进或完善普通法的适用。她立论的出发点,是强调衡平法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引发的两套法律规则间的不一致与不协调,从而给法律体制带来失去“理性的内在统一性”之风险(115)。因而,她认为普通法与衡平法的融合,将在最大程度上使法律的发展更具有“一致性、原则性与理性”,并更能达到法律背后的政策性目标(116)。沃芬顿教授亦同时强调,她并不是在主张一场“革命式”的改革,她认为这只是趋势、是航向,而达致的方式依然是通过法官们循序渐进的司法实践(117)。
2.“不可取代论”:衡平法无法替代的基因——“良心”
另一种声音,则来自传统的(或曰正统的)衡平法学者,如南安普敦大学的哈德森教授与剑桥大学的维戈教授,以及权威著作《施奈尔论衡平》,他们均不认为衡平法与普通法有在实体规则上融合的必要,甚至认为衡平法的独特性与其独特使命使得这种融合非但不必要,而且不可能。
哈德森教授一直强调作为衡平法核心内涵的良心,认为即使历经世纪的变迁,衡平法的最终使命,依然是对那些违背良心的行为说“不”(118)。他甚至不同意梅特兰与埃瓦舍勋爵认为衡平法乃普通法之补充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衡平法的产生与发展历史已经表明衡平法并非作为“普通法的影子”而存在,诸如信托、产权禁反言、禁制令等衡平规则体系,它们纯属衡平制度,与普通法毫无关联,自成一体(119)。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梅森(Mason A.)亦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衡平法上有关良心与公平等原则,使得法律能够自我调试,以适应一个自由与民主社会的不同需求(120)。
维戈教授则认为衡平法继续作为一种区别于普通法的存在,富有实质意义,他认为将衡平法中的某些早已稳定而成熟的法律制度(如信托制度)融入普通法中,其结果只会使得法律变得复杂,同时还失却了“该法律制度原有的精妙与细微之处”(121)。因而,维戈教授还是回到梅特兰对普通法与衡平法之关系的基本观点,即衡平法并不作为独立的法律制度而存在,其存在意义在于当普通法的适用将带来非正义之结果时,对后者提出矫正(122)。
《施奈尔论衡平》似乎集哈德森教授与维戈教授的观点于一身,一则认为衡平法的细微与精妙难以被着重规则的普通法所涵盖,再则,在衡平法有关良心的内在性质上,该著述与哈德森教授持同一观念,即衡平法上合乎良心这一要求,为法律原则的发展“明确地注入了一种道德因素”,而这成为法官们在为适应社会新需要而发展衡平法原则时所倚赖的基本原则(123)。作为对上述“融合论”的综合回应,《施奈尔论衡平》总结道:“将衡平法纳入私法中的责任与财产权利这一更大的体系中,将引致失去早已明确于法律体系中之道德因素的风险,而这一道德因素在过去曾激发了法律原则的发展,而它亦可在未来继续发挥此益。”(124)
庞德在1905年发出的呼吁言犹在耳:我们必须以捍卫法律的同样努力“捍卫衡平”(fight for equity)(125)。上述传统衡平法学者如今所做的,分明是一场“衡平保卫战”,而这些战士们手中最后的“王牌武器”,竟然就是衡平法无法被普通法替代的基因——“良心”。
结语:那种“冰川移动”的力量
卡多佐在描述判例法的发展道路时说:“它一步一步地向前进。衡量它的效果必须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为尺度。如果这样衡量,人们就看到其背后是冰川移动(the moving glacier)的那种力量和压力。”[7]从上文对自17世纪以来衡平司法风格与传统的回顾中,可以看到这种“冰川移动”的路径——衡平法在几个世纪中呈现出两条若隐若现的发展脉络:
一为主线,即衡平法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随着判例汇编体系的日趋稳定与全备,在不同年代法官的手中,走向规则化。该规则化的过程徐历至少三代法官,从17世纪奠定基石与框架的诺丁汉勋爵,到18世纪哈德威克勋爵的完善,再到19世纪埃尔登勋爵将该规则体系推至极致。当被推到规则化的顶点后,站在20世纪的门槛上,法官与学者依稀开始反省:衡平法是否走进了几个世纪前普通法曾踏入的“死胡同”?因而,在此背景下,20世纪的衡平司法,在经历了前半叶的僵化惯性后,出现了让衡平法回复自由、恢复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呼声。这种在规则以下潜移默化地运行的衡平思维,成为了规则化主线之外的第二条发展脉络。这条脉络,实际上从未偏离主线的走向,只是在不同时期,因着法官司法风格的不同,或明或暗,或强或弱。但不论强弱,它始终客观地存在。
那么,是什么背后的“力量和压力”在推动着衡平法这一“冰川”在这两条脉络中游走呢?答案是衡平法产生之源起、历经若干世纪的若隐若现、却依然贯穿衡平法始终的“良心”。试问:衡平灯火熄灭之时,是否亦代表着司法中“良心”的泯灭呢?
本文愿以庞德一个世纪前为衡平发出的呐喊作结:“法律需要以衡平调和,就如正义需要以怜悯调和。如果如某些人所声称,怜悯是正义的一部分,我们也同样可以说,衡平是法律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法律体系的运作都需要衡平的参与。在此衡平法衰落的时代,我们这些拥有形塑法律力量之人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丝毫不亚于那些曾经为衡平法奠基、将其推进与使其规则化的人们。”(126)
作者简介:
薛张敏敏(1978- ),女,香港永久居民,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3;香港浸会大学法学讲师,研究方向:法理学,普通法。
注释:
①⑥梅特兰在他的《衡平法》讲义中如此界定衡平法:“因而我们不得不这样讲,如今的衡平法,是指由我们英格兰法院施行的一套规则,而这套规则,如果不是因为《司法组织法》的实施(而将普通法法院与衡平法院合并),则仅由衡平法院施行。”Fredrick W.Maitland,Equity:A Course of Lectures,2nd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p.1.
②Alastair Hudson,Equity and Trusts,8th ed.,Routledge,2015,p.37.
③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Hart Publishing Company,1998,pp.228-229.
④R v.Wilkes(1770) 4 Burr.2527,p.2566.
⑤John H.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4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98.
⑦《大宪章》1215年版本的第39条及1225年版本的第29条。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大宪章》分条目,是英文版本中的做法,在其拉丁文版本中,并不存在条目的划分。
⑧28 Edw.III(1354),c.3,42 Edw.III(1368) ,c.3,参见:John H.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4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98.
⑨坎特伯雷大主教问:“陛下,您能本着仁慈(或译“怜悯”)之心运用权力以在判决中实现法律和正义吗?”女王回答:“是的,我能。”参见:Alfred T.Denning,The Road to Justice,Stevens & Sons,1955,p.5.
⑩John H.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4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98.
(11)尽管在都铎王朝时期出现了星宫法院(Star Chamber),行使衡平法上的刑事管辖权,但这只是历史之一瞬,很快就在一片反对声中被废除了。
(12)John H.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4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97.
(13)Fredrick W.Maitland,Equity:A Course of Lectures,2nd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p.4.
(14)即衡平法最为著名的法谚:"He who comes to Equity must come with clean hands."
(15)埃叙伯纳(Ashburner W.)在其经典著述《衡平法原则》(Principles of Equity)中,对作为衡平法基石之“良心”有着具体的描述。他概括了四种衡平法会因“良心”之故介入的四种情形:(1)“如果某人出于信任而将财产交托我手,让我为另一人之利益而处置财产,或是我已声明将为该另一人之利益而处置财产,那么,倘若我日后否认这一义务的存在或是意图为自己的利益而持有该财产,我的良心将因此蒙污。”(例如衡平法中的信托制度(trusts));(2)“如果我在接受财产担保的情况下借出钱财,那么当我因变卖该担保物而获得任何超出债务范围(包括其中的利息、必要的收费与开销)的利益时,保留这些超额的利益将违背我的良心。”(例如衡平法中有关回赎权(redemption)的规则);(3)“如果我已承诺履行某项义务,那么当我获得任何与履行该义务相矛盾的利益时,我的良心则被触及;而衡平法院为防止我的良心蒙受哪怕是最轻微的污渍,则将从我手中取走那些我业已获得的利益。”(例如因不当得利而获得的衡平救济,即返还原物(restitution));(4)“如果我因欺诈(实际的或推定的欺诈)、或因对他人施加不当影响(实际的或推定的不当影响)而获得利益,那么我若持有这些利益则违背我的良心。另外,即使我获得某财产时并未违背良心,但亦可因继续持有该财产而违背良心。因而,我因无过错的错误陈述而获得的财产,应当被归还予其最初的主人。”(例如因无过错错误陈述而获得的衡平救济,即允许解除协议(rescission))。参见:Denis Browne eds.,Ashburner's Principles of Equity,Butterworth & Co.,1933,p.39.
(16)Earl of Oxford's Case(1615) Ch.Rep.1.有关此案的阐述亦可参见杨福林:《在自由与权力之间——17世纪英格兰普通法的危与机》,载《河北法学》,2016年第1期第153页。
(17)Earl of Oxford's Case(1615) Ch.Rep.1,pp.5-10.
(18)代表衡平法院的埃利斯密尔勋爵与代表普通法院的时任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在1616年那场著名的衡平法与普通法的优先顺序之争,最终由国王詹姆士一世解决,衡平法的优先适用从当时被首次确定一直持续到今日。参见1981年《高级法院法》第49条第(1)款。
(19)Earl of Oxford's Case(1615) Ch.Rep.1,p.4.
(20)另外,该判词还展现了当时衡平法判决的另一风格,即尚存留大量的宗教成分,如依然保留对《圣经》的引用,“上帝的律法”(The Law of God)、“上帝荣耀的彰显”(Manifestation of God's Glory)等表达亦随处可见。Earl of Oxford's Case(1615) Ch.Rep.1,pp.4-7.
(21)Mich.31 Hen.VI,Fitz.Abr.,Subpena,pl.23,参见:John H.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4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08.
(22)William S.Holdsworth,Some Makers of English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147.
(23)其中最广为援引的是三个经典判例:Cook v.Fountain(1672) 3 Swanst.586; Howard v.Duke of Norfolk(1681) 2 Swanst.454; Nurse v.Yerworth(1674) 3 Swanst.608.
(24)Cook v.Fountain(1672) 3 Swanst.p.600.
(25)William W.Hening eds.,Richard Francis' Maxims of Equity,Richmond,1823.
(26)Ballow,A Treatise of Equity,Mifflin & Parry Printers,1831.对该书的描述,参见:William S.Holdsworth,A History of English Law,Vol.xii,Methuen & Co,1903,pp.192-193.
(27)William S.Holdsworth,Some Makers of English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176.
(28)William S.Holdsworth,Some Makers of English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p.183-184.
(29)William S.Holdsworth,Some Makers of English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183.
(30)Kerly,History of Equity,p.167,in William S.Holdsworth,Some Makers of English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200.
(31)Ellison v.Ellison(1802) 6 Ves.656.
(32)Howe v.Earl of Dartmouth(1802) 7 Ves.137.
(33)Aldrich v.Cooper(1802) 8 Ves.381.
(34)Murray v.Lord Elibank(1804) 10 Ves.84.
(35)Brice v.Stokes(1805) 11 Ves.319.
(36)William S.Holdsworth,Some Makers of English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199.
(37)Gee v.Pritchard(1818) 2 Swanst 402,414.
(38)Re National Funds Assurance Co(1878) 10 Ch D 118,p.128.
(39)Alfred T.Denning,The Need for a New Equity,Current Legal Problems,1952,Vol.5,p.2.
(40)Roscoe Pound,The Decadence of Equity,Columbia Law Review,1905,Vol.5,p.20.
(41)相关判例可见:Milroy v.Lord(1862) 4 De G.F.& J 264; Saunders v.Vautier(1841) 4 Beav.115; Fletcher v.Fletcher(1844) 4 Hare.67; Knight v.Knight(1840) 3 Bear.148; M'Fadden v.Jenkyns(1842) 12 L.J.Ch.146; Salomon v.A Salomon & Co Ltd[1897] A.C.22.参见:Alastair Hudson,Equity and Trusts,8th ed.,Routledge,2015,p.332.
(42)Alastair Hudson,Equity and Trusts,8th ed.,Routledge,2015,pp.24-25.
(43)Ewing v.Orr Ewing(No 1)(1883) 9 App.Cas.34,p.40.
(44)Denis Browne eds.,Ashburnerg Prineiples of Equity,Butterworth & Co.,1933,p.18.
(45)Donoghue v.Stevenson[1932] AC 562.
(46)Macaura v.Northern Assurance Ltd[1925] AC 619.
(47)Cook v.Deeks[1916] AC 554.
(48)这两个判例是:George v.Skivington(1869) L.R.5 Ex.1; Heaven v.Pender[1883] 11 Q.B.D.503.而这两个判例最终被“唐纳修案”认可。
(49)Donoghue v.Stevenson[1932] AC 562,p.576.
(50)参见:《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9至37节。
(51)“唐纳修案”成为法律史上的经典判例之一,在案发的苏格兰佩斯里市(Paisley),还设有该案的主题公园,公园内最显赫的位置,摆放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埃特金勋爵那段著名的阐释“邻舍原则”的判词。
(52)较为典型的判例可见:Grey v.Inland Revenue Commissioner[1960] AC 1; Leahy v.Attorhey-General of New South Wales[1959] AC 457; Oppenheim v.Tobacco Securities[1951] AC 297.参见:Alastair Hudson,Equity and Trusts,8th ed.,Routledge,2015,p.40.
(53)Re Diplock(1948) Ch.465,p.481.
(54)Raymond Evershed,Reflections on the Fusion of Law and Equity After 75 Years,Law Quarterly Review,1954,Vol.70,p.330.
(55)Raymond Evershed,Reflections on the Fusion of Law and Equity After 75 Years,Law Quarterly Review,1954,Vol.70,p.330.
(56)Alfred T.Denning,The Way of An Ieonoelast,Sydney Law Review,1960,Vol.3,p.209.
(57)Alastair Hudson,Equity and Trusts,8th ed.,Routledge,2015,p.40.
(58)Alfred T.Denning,The Need for a New Equity,Current Legal Problems,1952,Vol.5,p.1.
(59)Alfred T.Denning,The Need for a New Equity,Current Legal Problems,1952,Vol.5,p.1.
(60)Re Diplock[1941] 1 Ch.267; Re Diplock[1944] AC 341.
(61)Thompson v.Earthy[1951] 2 KB 596.
(62)Armstrong v.Strain[1952] 1 T.L.R.82.
(63)Alfred T.Denning,The Need for a New Equity,Current Legal Problems,1952,Vol.5,pp.2-7.
(64)Alfred T.Denning,The Need for a New Equity,Current Legal Problems,1952,Vol.5,p.10.
(65)Bendall v.McWhirter[1952] 2 QB 466.
(66)National Provincial Bank Ltd v.Ainsworth[1965] AC 1175.
(67)Cobb v.Cobb[1955] 1 WLR 731.
(68)Pettitt v.Pettitt[1970] AC 777.
(69)Pettitt v.Pettitt[1970] AC 777.
(70)Karsales(Harrow) v.Wallis[1956] 1 WLR 936.
(71)Suisse Atlantique Société d'Armement Maritime S.A.v.N.V.Rotterdamsche Kolen Centrale[1967] 1 AC 361.
(72)Harbutt's 'Plasticine' v.Wayne Tank and Pump[1970] 1 QB 447.
(73)Photo Productions v.Securicor Transport[1980] AC 827.
(74)Ebrahimi v.Westbourne Galleries Ltd[1973] AC 360.
(75)Ebrahimi v.Westbourne Galleries Ltd[1973] AC 360,p.379.
(76)Ebrahimi v.Westbourne Galleries Ltd[1973] AC 360,p.379.
(77)威尔伯福斯勋爵的这段有关衡平法在公司法领域中提供救济之原理的判词,在当代许多重要案件中均得到遵循,例如:霍夫曼勋爵(Lord Hoffmann)在有关不合理损害救济的“奥尼尔诉菲利普斯案”(O'Neill v.Phillips[1999] 1 WLR 1092)中对其全文引用(参见该判决第1099页);香港终审法院最新的有关公司以“正当且衡平”理由清盘的“甘琨胜遗产案”(Kam Leung Sui Kwan v.Kam Kwan Lai[2015] 18 HKCFAR 501)(即一般所称的“镛记集团清盘案”)中,亦对威尔伯福斯勋爵与霍夫曼勋爵的判词全文引用(参见该判决第45段)。可见,前者对衡平法在公司法领域适用之阐释,获得了司法界的广泛认同。
(78)Louis Blom-Cooper & Gavin Drewry,Towards a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Law:The Reid and Wilberforce Era 1945-82,in Louis Blom-Cooper,Brice Dickson and Gavin Drewry eds.,The Judicial House of Lords:1876-2009,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09-231.
(79)Alastair Hudson,Equity and Trusts,8th ed.,Routledge,2015,p.332.
(80)Re National Funds Assurance Co(1878) 10 Ch.D.118,p.128.
(81)戈夫勋爵于1986年至1998年间担任上议院常任上诉法官,并于1996年至1998年间担任上议院首席大法官;布朗尼·威尔金森勋爵则于1991年至2000年间担任上议院常任上诉法官,并接任戈夫勋爵于1998年至2000年间担任上议院首席大法官。
(82)Tinsley v.Milligan[1994] 1 AC 340.戈夫勋爵在该案中所作为异议判词。
(83)White v.Jones[1995] 1 AC 207.
(84)Westdeutsche Bank v.Islington L.B.C.[1996] AC 669.戈夫勋爵在该案中所作为异议判词。
(85)White v.Jones[1995] 1 AC 207,pp.259-260.
(86)White v.Jones[1995] 1 AC 207,pp.268-269.
(87)Westdeutsche Bank v.Islington L.B.C.[1996] AC 669,p.696.
(88)Westdeutsche Bank v.Islington L.B.C.[1996] AC 669,p.697.
(89)Alastair Hudson,Equity and Trusts,8th ed.,Routledge,2015,p.41.
(90)Westdeutsche Bank v.Islington L.B.C.[1996] AC 669,p.705.
(91)White v.Jones[1995] 1 AC 207,pp.259-260.
(92)White v.Jones[1995] 1 AC 207,p.275.
(93)Alastair Hudson,Equity and Trusts,8th ed.,Routledge,2015,pp.40-41.
(94)Brice Dickson,A Hard Act of Follow:The Bingham Court 2000-2008,in Louis Blom-Cooper,Brice Dickson and Gavin Drewry eds.,The Judicial House of Lords:1876-2009,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56.
(95)Brice Dickson,A Hard Act of Follow:The Bingham Court 2000-2008,in Louis Blom-Cooper,Brice Dickson and Gavin Drewry eds.,The Judicial House of Lords:1876-2009,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56.
(96)Johan Steyn,The Case for a Supreme Court,Law Quarterly Review,2002,Vol.118,p.382.
(97)例如:R(Hoxha) v.Special Adjucator[2005] 1 WLR 1063,一宗有关以为遭受与性别有关之暴力的阿拉伯妇女寻求庇护的案件。在若干案件中,黑尔男爵夫人作出了与四位男性同袍不同的异议判决,例如:R(Kehoe) v.Secretary of State for Work and Pensions[2006] 1 AC 42,其中涉及母亲向”缺席父亲”在儿童抚养问题上要求金钱资助的权利;M v.Secretary of State for Work and Pensions[2006] 2 AC 91,其中涉及一名女同性恋者是否可减少向其前夫支付儿童抚养费。还有一些有关儿童诱拐的案件,如:Re J.(A Child)[2006] 1 AC 80; Re D.(A Child)[2007] 1 AC 619; Re M.(Children)[2008] 1 AC 1288.参见:Brice Dickson,A Hard Act of Follow:The Bingham Court 2000-2008,in Louis Blom-Cooper,Brice Dickson and Gavin Drewry eds.,The Judicial House of Lords:1876-2009,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73-275.
(98)Jennings v.Rice[2003] 1 P.&C.R.100.
(99)Jennings v.Rice[2003] 1 P.&C.R.100,at[49].
(100)Jennings v.Rice[2003] 1 P.&C.R.100,at[56].
(101)例如:Cobbe v.Yeoman's Row Management Ltd[2008] 1 WLR 1752; Thorner v.Major[2009] 1 WLR 776.
(102)Stack v.Dowden[2007] 2 AC 432.
(103)Jones v.Kernott[2012] 1 AC 776.
(104)Stack v.Dowden[2007] 2 AC 432,at[64]-[65]; Jones v.Kernott[2012] 1 AC 776,at[8].
(105)Alastair Hudson,Equity and Trusts,8th ed.,Routledge,2015,pp.41-42.
(106)Gardner S.& Davidson K.,The Future of Stack v Dowden,Law Quarterly Review,2011,Vol.127,p.15.该文被引于:Jones v.Kernott[2012] 1 AC 776,at[16]-[17].
(107)Fredrick W.Maitland,Equity:A Course of Lectures,2nd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p.20.
(108)Peter Birks,Private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61; Peter Birks,Property,Unjust Enrichment,and Tracing,Current Legal Problems,2001,Vol.54,p.231; Peter Birks,Establishing A Proprietary Base,Restitution Law Review,1995,Vol.3,p.83.
(109)Alastair Hudson,Great Debates in Equity and Trusts,2014,Palgrave 2014,p.51.
(110)Alastair Hudson,Great Debates in Equity and Trusts,2014,Palgrave 2014,p.51.
(111)John McGhee eds.,Snell's Equity,33rd ed.,Sweet & Maxwell,2015,p.18.
(112)有关合同法中法律与道德关系回归的讨论,亦可参见于月红:《论英美合同法中约因的适用规则及启示》,载《河北法学》,2015年第3期第143页。
(113)John McGhee eds.,Snell's Equity,33rd ed.,Sweet & Maxwell,2015,pp.18-19.
(114)Graham Virgo,The Principles of Equity & Trus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5.
(115)沃芬顿教授着重强调了衡平法有别于普通法的四个方面的特殊性,即实体规则、救济策略、实施技巧以及程序方面的不同。Sarah Worthington,Equity,2nd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13-19.
(116)Sarah Worthington,Equity,2nd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321.
(117)Sarah Worthington,Equity,2nd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322.对沃芬顿教授这种整合的观点,华威大学的衡平法学者沃特(Gary Watt)教授提出了反对意见,参见:Gary Watt,Equity Stirring:The Story of Justice Beyond Law,Hart Publishing,2009,pp.84-87.
(118)Alastair Hudson,Great Debates in Equity and Trusts,2014,Palgrave 2014,pp.9-22; Alastair Hudson,Equity and Trusts,8th ed.,Routledge,2015,pp.22-28,1321-1323.
(119)Alastair Hudson,Equity and Trusts,8th ed.,Routledge,2015,p.40.
(120)Anthony Mason,The Place of Equity and Equitable Remedies in the Contemporary Common Law World,Law Quarterly Review,1994,Vol.110,p.238.
(121)Graham Virgo,The Principles of Equity & Trus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5.
(122)Graham Virgo,The Principles of Equity & Trus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5.
(123)John McGhee eds.,Snell's Equity,33rd ed.,Sweet & Maxwell,2015,p.20.
(124)John McGhee eds.,Snell's Equity,33rd ed.,Sweet & Maxwell,2015,p.20.
(125)Roscoe Pound,The Decadence of Equity,Columbia Law Review,1905,Vol.5,p.35.
(126)Roscoe Pound,The Decadence of Equity,Columbia Law Review,1905,Vol.5,p.35.
(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17年第2017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