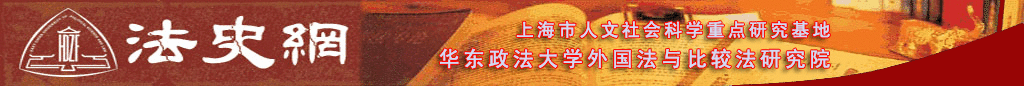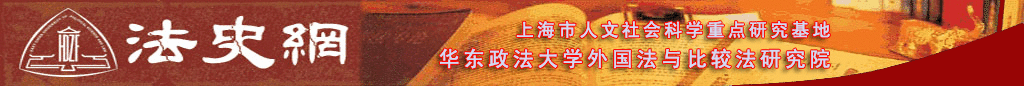内容提要:
宋代府州一级审判一般有推勘、录问、检法、拟判、审核、判决六道程序。“推驳(推正、驳正)”制度是理解当时司法程序的枢纽。法司“驳正”与录问“驳正”针对府州鞫司的“鞫狱不当”。鞫司针对下级机构的“推正”和府州内诸鞫司之间互相移推是“推正”的二种类型,宋代法律从正面直接规定了录问官的驳正权。“定夺驳正”主要是针对“入人死罪”的情形。其上的幕职官及通判以“定夺”程序纠正“检法不当”,而不是“别推”。“定夺驳正”是“当职官”以程序权力“驳正”冤案。开封府幕职官以推鞫为业,对刑事案件有建言权。“鞫谳分司”不排斥长官与副职参与,有长贰参与的聚议制度是长官制体制大背景所引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展示各方意见的好平台,可供长官做最后定夺。关注鞫、谳之外的其他程序,包括录问官与录问程序,幕职官的角色与作用等,不忽略其他官员或机构的存在和贡献,是正确、适度评价“鞫谳分司”及鞫谳双方作用所必须坚持的立场,“鞫谳分司”是我国古代“听”“断”合一与分立的重要体制。
关 键 词:
“鞫谳分司”/“推驳”/“定夺驳正”/“当职官”/“幕职官”
标题注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C023),辽宁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基础理论研究课题。
鞫与谳是司法中最重要的两道程序。其实,在鞫、谳之间,即鞫之后、谳之前,一般还要插入录问;检法之后,还有拟判;之后是聚议,最后呈上长官。以州为例,有学者归纳了宋代审判的六道程序:“鞫司审明案情,再由另外的法官(一般是选邻州官员)录问核实,转法司检出适用法条,再由其他官员拟判后,经同级官员集体审核,呈长官判决。”[1]程序依次是:鞫司推勘—邻州官录问—法司检法—他官拟判—同级集体审核—长官判决。
一、“推驳”制度下的“当职官”
谳司权力既如上述,从程序角度梳理一下所有相关官员的角色及责任,尤其抓住“推驳(推正、驳正)”制度,是理解当时司法程序的枢纽。
1.鞫司权力、责任与“推正”制度
法司“驳正”和录问“驳正”都是针对司理、录事参军等府州鞫司的,这对他们似乎有些苛刻。如《断狱敕》规定:“诸录事、司理……参军(州无录事参军,而司户参军兼管狱事者同),于本司鞫狱……有不当者,与主典同为一等。”[2]这是对府州鞫司鞫狱过程中“公务连坐”办法的规定。录事、司理参军两个鞫司“鞫狱不当”,官员要同吏(主典)同等坐罪。而且,需要特别注明“司户参军兼管”州院鞫狱要与录事参军主管司法一样承担责任。
不过,府州鞫司直接收案的不多,大多是接受属县移送的徒以上案件。对严重“入罪”比如“入人死罪”案件的“推正”,在其职掌中最为显眼。宋代《赏格·命官》有专条,鞫司“任内推正县解杖、笞及无罪人为死罪者(累及同)”,根据“推正”死罪或牵累死刑的人数多寡,分别给予“陞半年名次、免试、减磨勘二年”等行政性奖赏。对于吏人,若能“推正”属县解送来杖、笞刑及无罪人为死罪者,“累及五人,转一资”[3]。
这种可能发生于诸州司理与录事参军、开封府左右军巡院等鞫司职守上的好事情,多少给这个机构以主动、积极的色彩。同法司的“驳正”一样,鞫司针对下级机构,可以做“推正”工作。
“推正”又指“别推”及“移推”。“别推”也称“移司别推”,指府州内诸鞫司之间互相移推,比如,州司理移至录事参军,或录事移至司理参军,开封府左巡移至右巡,或右巡移至左巡,或左右巡移至司录参军等。临刑称冤及家属声冤的,须由监司派官复审,称“移推”或“差官别勘”。
对于推正,《赏令》规定凡推鞫中“元不议大情”而“入人死罪”的案件,“官吏别推能推正”的,其“推者准‘非当职官及吏人驳正格’”理赏。官员的赏赐分别是:减磨勘二年、转一官、奏裁。如果“入人死罪”属于下述情形,推鞫中“虽议大情而止作疑似,或因疑似举驳及翻异称冤而推正者”,比照前述《驳正格》降等理赏,即“各二人理一名。止一名者,命官免试,吏人指射优轻差遣一次”[4]。对“入人徒、流罪”案件,若官员“因别推而能推正者,各累及七人比大辟一名计数推赏”[5]。
2.录问“驳正”“定夺驳正”与“驳正”制度
第一,录问官“驳正”——法司驳正前最重要的“驳正”。
学界对录问已经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徒以上案件应从“邻州选官”录问,京师地区一般选差御史台官录问;地方重大死刑案犯,要求知府、通判、幕职官共回录问即实行“聚录”之制;有的案件聚录之后还得再录问一次;甚至录问官的责任比检法官要大得多,因为错案追究时,录问官处罚比检法官更重。[6]
录问官的驳正权由法律从正面直接规定。依《断狱敕》:“诸置司鞫狱不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即审问(非置司同),或本州录问者,减推司罪三等(当职官签书狱案者,与出入罪从一重)。”[7]很明显,录问官“驳正”针对的是案情。“鞫狱不当”不是指适用法律不当,而是“推司”审定的案情有问题,从而可能导致“罪有出入”。在责任上,外请的录问官司不能驳正,减推司罪一等,本州录问的,减推司罪三等,这采取的是内外录问有别的原则。
按宋《赏令》:“诸入人徒、流罪或配已结案(谓将杖以下及无罪或不该配人,作徒、流配罪勘结者),而录问官吏(元勘当职官非。下文据此)能驳正……者,各累及七人比大辟一名计数推赏。”[8]据此,录问官吏因与原来的勘鞫官无关,故能驳正;驳正也仍然是严重“入罪”的案件,问题仍出在案情审定方面。
第二,“定夺驳正”。
检法驳正与录问官司驳正都针对“鞫狱不当”,其只是驳正的两种情形。在《前述赏令》中与“别推能推正”一同规定的,还有“驳正”制度,亦称“定夺能驳正”。
“定夺驳正”主要是针对“入人死罪”的情形。凡推鞫“元不议大情”,而官吏“定夺能驳正”,其“定者准‘非当职官及吏人驳正格’”理赏。官员赏赐分别是:减磨勘二年、转一官、奏裁。如果“入人死罪”属于下述情形,推鞫中“虽议大情而止作疑似,或因疑似举驳及翻异称冤而驳正者”,比照前述《驳正格》降等理赏,即“各二人理一名。止一名者,命官免试,吏人指射优轻差遣一次”[9]。同时,《赏格》规定:“诸色人入人死罪而吏人能驳正者,每人转一资。”[10]对于能驳正的吏人,也予行政奖励。
3.“推驳”制度与“当职官”
我们应该对司法诸环节的“不当”类型与范围,进行一下梳理,这可以帮我们了解与之相应的推正、驳正由谁来做的问题。梳理内容见表1。
从法条中抽象出的诸种“不当”来看,对“鞫狱不当”有录问官司驳正,检法驳正;而对于“检法不当”,检法官司不可自己来做,必须由他官来做,那很可能是由其上的幕职官及通判来进行的,程序可能是“定夺”,而不会是“别推”。按《赏式·保明推正驳正入人死罪酬赏状》:“见得推鞫或检断不当,如何驳正或推正”[11],则“推鞫不当”有“推正”,“检法不当”有“驳正”。当然,“推鞫不当”也可“驳正”,比如检法驳正。
另外,上述法条中出现了“当职官签书狱案者”“签书官吏”,涉及法律中使用很普遍的“当职官”一词。那么,“当职官”的含义是什么?所指为谁?范围多大?
扩大些说,“当职官”指“当职官吏”,可以具体化为“前推及录问官吏”,或“检断、签书官吏”;也可以分称“当职官”“吏人”或“命官…‘吏人”。这些都是宋代法律用语。不过,由于我们重点分析“官”的角色,只是附带谈“吏人”,所以用词仍以“当职官”为主。
“当职官”一词显示着官员在程序中的角色。在此,它与“诸曹官”“幕职官”产生了交叉。第一,若称“元勘当职官”,即原初鞫狱官,在州指州司理参军、录事参军,甚至有司户参军,其涉及大部分“诸曹官”尤其涉及全部鞫司。第二,若称“当职官签书狱案者”,指实际鞫问官之外的其他职官。可以是录事参军“连书”司法参军的检法,也可以是司理参军“连书”没有实际参与的推鞫。第三,“当职官”连坐时,法律规定“官司失入死罪”分为四等:为首当职官、第二从当职官、第三从当职官、第四从当职官,首犯与从犯的每一等别之行政责任,依据失入人数多少,各不相同,有勒停、冲替、差替、追一官勒停、追两官勒停。[15]这时的“当职官”,包括所有参与案件鞫勘、检法、录问甚至签书的官员。其中大部分是诸曹官,“签书”者可能还会包括通判及幕职官(签判及推官、判官等)。

“当职官”即“直接当事职官”,指经手官员,也有“州县当职官”或“监司、州县当职官”等说法。前述《赏令》“当职官”注释“谓非长吏”;《赏格·命官》“当职官”注释“谓州非知州,通判、职官之类”[16],意谓在诸州中,“当职官”即“非知州”,指“通判、职官之类”。与前一注释的共同之处是“非长官”“非知州”,其指出了“通判、职官之类”的范围。结合前述府州官制,应当包括通判、幕职官、诸曹官。则除了知府、知州之外,府州副职的通判、幕职官、诸曹官均可以是“当职官”。证之以前述“前推及录问、检断、签书官吏”的说法,通判之外的“当职官”,首先包括“诸曹官”,比如两“推司”(此处的“前推”)的录事参军、司理参军,“检断”的司法参军;司户参军若任鞫司,也在其内。录问官可能来自诸州,官职不定,实例中有州通判,也有知县;若来自本州府,则其官职至少应是“诸曹官”级别,或即由“幕职官”充任。在检法阶段,“签书”官可以是府州录事参军;在此之外的场合,可以是“幕职官”。全部“幕职官”都可以是“签书”官。“签书”意味着共同负责,所以他是分担责任者。
“当职官”与驳正的关系体现在法律规定的“当职官以议状驳正”与“非当职官能驳正”,其实,还有前述的“定夺驳正”。
“定夺驳正”是“当职官”以程序权力“驳正”冤案。我们从案例中可以推知这一程序。“幕职官”对“诸曹官”鞫谳的审核就属于这种“定夺”。
“当职官以议状驳正”是明确见诸法律的。《赏令》规定:“诸入人死罪,而当职官(谓非长吏)能以议状驳正者,比类‘非当职官赏’奏裁。”[17]案例中也有与此类似者。例如,蕲州知州王蒙正诬陷林宗言死罪的冤案,司理参军刘涣未反对,但对案件有疑问,写有“议状”。案件平反后,刘涣以曾有“议状”免追官。①虽然这不能解释为“驳正”冤案,但书拟“议状”,提出疑窦,毕竟不同于同恶相济,所以免其“追官”处罚。关于“议状”驳正,可以理解为府州录事、司理、司法、司户参军等“诸曹官”及“幕职官”均有权这样做。
“非当职官驳正”是个复杂的问题。《赏格》规定:“入人死罪而非当职官(谓州非知州,通判、职官之类),能驳正者(累及同):一名,减磨勘二年;二人,转一官;三人以上,奏裁。”[18]法律不是正面规定“当职官驳正死罪”,而是规定“非当职官能驳正者”。那么,该如何看待“非当职官驳正”这一赏赐规定的立法体例?
在道理上,“当职官”驳正是责任和义务,故无赏是可以理解的;法律规定对“非当职官能驳正者”给予赏赐,顺理成章。在宋代法律中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形:“应当”的职责履行,没有赏赐。比如,“本院”即使推正了自己“已结正、未录问间翻异称冤”的案件,也不能算“推正”,因为这是它的职责与义务,不值得嘉赏。赏赐针对“非当职官”,即针对没有该义务的人。可以理解为:如司理参军鞫狱不当,另一个鞫司录事参军如果提出意见和建议,它本身的身份就是“非当职官”,“当职官”自然是司理;反之亦然。这可能就是制定上述专门法律一《赏格》的原因和体制机制背景。法律中指称它时,或称它为《非当职官及吏人驳正格》[19],或称它为《非当职官赏(格)》;以至于“当职官(谓非长吏)能以议状驳正者”,也要“比类‘非当职官赏’奏裁”[20]。因为“当职官以议状驳正”只是“当职官驳正”的情形之一,最正常的是程序中直接“驳正”,不借助“议状”,这样后者就不必“比类”了。
4.“幕职官”的拟判、推鞫、案覆权与“定夺”驳正
无论法司后来是否被禁止拟判而只剩下检法事务,在宋代,除了法司拥有书拟权外,幕职官还享有拟判权。同时,官员集体审核的聚议,也涉及幕职官。讲鞫谳分司,绕不开幕职官。
幕职官的名称、范围及职权,地方州军与开封府等有所不同。
第一,地方诸州、军的幕职官。
在地方诸州、军,“幕职官”包括“签书判官厅公事”,及“两使、防、团、军事推判官”等各种推判官;在职级、地位上,他们高于录事、司户、司理、司法等“诸曹官”;在职责上,他们“掌裨赞郡政,总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于其长而罢行之”,相当于处理文案事务的秘书长,工作内容及范围十分广范,兵刑钱谷皆在其中。因而有关司法一事在权力划定或享有上对他们来说,属于兼职。
签书判官厅公事(签判)及各类推官、判官等幕职官,包括节度判官、防御判官、团练推官、团练判官、观察推官、军事判官、军事推官等,其协助知州、知府作出初步判决意见,这种行为称为“拟判”或“书拟”。
首先是签判书拟。“签书判官厅公事”这个官名大抵也正好反映了它的这一职责。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不少签判书拟。例如其卷七题名“拟笔”的《出继子不肖勒令归宗》,文首云:“昨来佥厅择状之日”,“及佥厅责令面对”,其后“唤到”证人,“审会”族长等状,都似乎由佥厅进行。文末云:“准令:诸养同宗昭穆相当子孙,……若所养子孙破荡家产,不能侍养,及有显过,告官证验,审近亲尊长证验得实,听遣。今来石岂子所犯,委是有伤风教,令照条施行。欲将石岂子押下巴陵县,遣还所生父母,取管状申。取台旨。奉徐知郡台判:石岂子无状如此,何可不断?勘杖一百,勒令归宗。余照所拟行。”[21]此处的前半部分是检法和拟罪,最后是知府判断;刑罚由知府确定,其余照书拟执行。大抵是佥厅鞫勘(当是复核而不是初审)检法书拟,知府最终决断。
其次是推官、判官书拟。孝宗时,陈希点为平江府观察推官,与固执的太守丘公屡争狱事,“至于再三,竞不能夺。自尔,公所书拟,望而许之”②。争执久了,知府认为推官正确率高,干脆一律予以认可。这是个案,但具有一定代表性。当然,长官可以“以书拟未当而不判”。
除了大量的拟判事例外,宋代案例还反映出推官、判官还有推鞫、案覆等司法权,他们参与司法的机会,大抵也有两种。
一是推判官受知州之命推鞫本州军案件,成为推司。比如,知蕲州王蒙正故人林宗言死罪案,判官尹奉天接受知州将林宗言问称死罪的吩咐,投其所好,逼迫林宗言就范,成为王的帮凶。案件平反后,尹奉天被“追两任官”③。
还有,据《宋史·罗必元传》记载,罗必元“调福州观察推官,有势家李遇夺民荔支园,必元直之”④,则推官享有民事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权。这里,尚不清楚是受知州委任,还是主动承接民人诉讼。
二是府州推判官被监司借调案覆大狱。据《折狱龟鉴》第八卷《矜谨·张奎辨牍》记载,张奎“为常州推官,转运使举监衢州酒税。婺州有滞囚,法当死,狱成,再问辄不服。命奎覆案,一视牍而辨之,得不死”。《宋史·姚仲孙传》记载,姚仲孙“调邢州推官,徙资州。转运使檄仲孙诣富顺监按疑狱,全活数十人。资州更二守,皆惽老,事多决于仲孙”。推官之所以有机会受监司之命断决刑事案,是因其本职有断案经历;另外,推官的辅佐知州的角色,从“事多决于仲孙”也可知晓。⑤
第二,开封府幕职官。
在开封府,知府具有重要而特别的司法、治安职责,据《宋史·职官志六》所载“中都之狱讼皆受而听焉,小事则专决,大事则禀奏。屏除寇盗,有奸伏则戒所隶官捕治”[22]。完成这些任务当然需要辅佐,“其属有判官、推官四人,日视推鞫,分事以治,而佐其长”[23]。可见,开封府幕职官以推鞫为业,职事较州军判官、推官更为专业。
案例表明,京府判官对刑事案件有建言权。据《折狱龟鉴》卷六《核奸·李兑解缢(李应言一事附)》所载:“李应言谏议为开封府判官时,京师富民陈氏杀佣作者,而诬以自经死。事觉,辄逃匿不获。应言指其豪横,交结权要,请严捕之。”可见,建言抓捕符合其辅佐知府的职守。据《折狱龟鉴》卷八《矜谨·李应言按妖(荣谩、吴育二事附)》所载:“荣谩大监为开封府判官时,太康县捕民数十人,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名‘白衣会’。知府贾黯疑其有妖,请杀为首者,余悉流之。谩以为本无妖。黯具奏,并谩议奏之。朝廷以谩议为是,乃流其首,余皆杖之。盖郓州之民传妖法,无不轨事;太康之民事浮屠法,本无妖,故轻重之差如此。若非矜谨,则或以为不轨,而尽诛其党;或以为有妖,而特杀其首,不无枉滥矣。”[24]这是在聚议时,判官发表了与长官不同的意见。好在长官能容,将两种意见都奏上,朝廷后来选择的恰恰是判官的处理意见。⑥
第三,幕职官“定夺驳正”问题。
关于幕职官的司法参与度,有个数据可资参考。《折狱龟鉴》中,全部都享有司法权的录事、司理、司户、司法参军等“诸曹官”,出现频率较高,总数19人,包括录事4人、司理11人、司法1人、司户2人、开封府仓曹1人(特例);“幕职官”出现10人(11人次),包括开封府判官2人,诸州军事推官2人、节度推官1人、团练推官1人、观察推官1人、推官3人。两下相比,后者数量是前者的一半,出现频率较高。因此,在重视司理、录事、司法参军等“诸曹官”司法职能发挥的同时,也不宜忽略“幕职官”的司法参与情形。
幕职官“定夺驳正”一是府州推判官被监司借调“案覆”,这时可能是“置司”鞫狱“张奎辨牍”的推官“覆案”,姚仲孙至富顺监“按疑狱”,皆是如此。二是在本府州内的“覆决”。这反映了幕职官对“鞫司”权力的有效掣肘不亚于录问官、法司等的驳正。这是因为:对于鞫司勘定(“州命录事参军鞫之”),且经过了“州官审覆无反异,皆以为得实”(可能经过了录问、检法程序,甚至经过了聚议,尤其是获得了长官知州首肯)的案件,推官仍有权力决定其案件走向——“数日不决”。原因是:一则,推官享有“拟判”权,这是基础。“判决”不草拟出来,知州除了“屡趣之”之外也无可奈何。二则,在制度上保持一种鞫推、录问、检法、聚议之后,仍有职官“覆决”以“定夺”的环节,这是在长官决断之前留给职官驳正的最后机会。
5.长贰参与的聚议
“鞫谳分司”不排斥长官与副职参与,大理寺“左断刑”甚至将长贰作为“议司”的重要参与者,作为与“断司”相对的机构或程序。据《宋史·职官志五》所载,光宗绍熙间(1190-1194年)规定,“将八评事已拟断文字,分两厅点检。或有未安,则述所见与长、贰商量”[25],“断司”鞫问的结款有不妥或疑窦之处,要当面向长贰汇报看法,提出意见或建议,以供定夺。这仍然是“鞫谳分司”程序的应用,不过是“两厅”各“述所见与长、贰商量”,多了一道中间分拣、检查过程。可以概括为长贰参与的聚议。
这种“聚议”制在行政事务中被普遍要求使用,但也有属于司法范畴的情况。据《宋史·职官志三》所载,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诏:“户部事有可疑难裁决者,许长贰与众郎官聚议,文字皆令连书,有定议,然后付本曹行遣。”虽然这不是专对治狱而发,但正如前述,户部事务有许多民事争讼要处理,这也属于司法业务范畴。[26]
地方府州军发生于诸曹官、幕职官与长官的司法意见之争,有的是一对一的场合,有的则可能是在众人在场的“聚议”场合。
据《宋史·崔与之传》所载,“民有窘于豪民逋负,殴死其子诬之者”,这是不得已的苦肉计。提刑对案犯“欲流之”,“小民计出仓猝”,一时打错算盘,何“忍使一家转徙乎?况故杀子孙,罪止徒”,故意杀死子孙也不过徒罪,不必一定处以流刑。长官最终被说服。⑦
这些范围不等的聚议制度,其出现一方面是长官制(或长官负责制)大背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聚议对展示各方意见是好平台,可供长官做最后定夺。
总之,关注鞫、谳之外的其他程序及包括录问官与录问程序,幕职官的角色与作用等,不能忽略其他官员或机构的存在和贡献,这是正确、适度评价“鞫谳分司”及鞫谳双方作用所必须坚持的立场。
二、对“鞫谳分司”机制的评定
南宋高宗时周林、汪应辰对“鞫谳分司”的评价是人们常引用的,也是人们认识和研究该制度的基础。但两者所述的“鞫谳分司”是有差异的,前者主狭义,后者则广义狭义并用,我们不能等同视之。
1.关于周林奏章
《历代名臣奏议》收录了周林四道奏章,题目分别为《论时不可失》《论行赏当先战士而后主将》《奏推司不得与法司议事札子》《奏疑狱札子》。四者之中,后两道涉及法律,一个属于司法,一个属于司法加立法;评论“鞫谳分司”的是第三道奏章。
周林,《宋史》无传。按通常说法,他是北宋末宣和三年(1121)科举“诸科”出身,而其活动主要在南宋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一绍兴二年十二月戊戌条,载宋高宗“召试”左宣教郎洪兴祖、左承事郎孔端朝、左文林郎张炳、左从事郎周林四人之事,“上览策,谓大臣曰:‘兴祖所论谠直,切中时病,当为第一。’遂与端朝并除(秘书省)正字,而炳、林令吏部与诸州学官”⑧。经过殿试的周林,是否到州府任学官,史阙有间,未知其详;但司理参军、州学教授多为进士初任或再任官职,殿试出任教授相当于再任或再调,其能够出任又可据惯例推知。
周林奏章不知何时所作,内容相对简单。以称颂语起始:“虞舜恤刑,文王慎狱。陛下用舜、文之心,赐哀矜之治;遣平反之使,议殿最之法,可谓至矣”,接着是有关“鞫谳分司”的主体内容:
然而州郡之间,刑狱之地,尚有循习旧态,因仍故事,为民大害,未能仰称天地宽厚之德,臣窃惜之。狱司推鞠,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然而推鞠之吏,狱案未成,先与法吏议其曲折,若非款状显然如法吏之意,则谓难以出手。故于结案之时,不无高下迁就、非本情去处。臣愿严立法禁:推司公事,未曾结案之前,不得辄与法司商议。重立赏格,许人告首。[27]
首先,周林针对的是州郡,所以“狱司”“法司”只指府州司理、录事和司法参军。他的州学官(州学教授)及严州知州的经历,尤其是后者,是他提出该实践问题及相应对策的经验基础。其他佐证是,本道奏章的后半部分讲到“狱吏惨刻”,其也指州郡。第四道奏章讲的是“诸路疑狱”,建议废除“不应奏而奏”罪名。虽然他反复提到州郡和大理寺,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州郡:州郡“以请谳之责为虑”,因担心被责,所以干脆不奏;大理寺“以简牍之繁为劳”,你不奏我省事。[28]对于熟悉地方事务的周林,州郡是他考虑的重点。
其次,周林指出“狱司推鞠(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两司分立的目的是“防奸”。“奸”是谁?是狱司。周林觉得推司为规避风险,“案成”之前与法司商议,并揣摩法司心思,这造成一味顺从法司意见,致使本应有的牵制、制约制度名存实亡。为此,他提出立法禁约建议:不准推司在狱成之前与法司商议案情;而且要允许人们告发。
之所以是“狱司”或“推司”首先出问题,是因为“鞫谳分司”给推司造成的压力是巨大的。
2.关于汪应辰奏章
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右司郎中汪应辰《论刑部理寺谳决当分职札子》对鞫谳分司的评价在时间上要比周林奏章晚;在内容上,其指涉范围更广,不限于推司与法司,因而更应重视。
汪应辰(1118-1176)是高宗绍兴五年(1135)的进士,授镇东军签判,召为秘书省正字。当时秦桧主和议,汪应辰上疏主张抗金,力言因循无备、上下相蒙、不明敌势之可畏,忤秦桧意,出为通判建州、静江府、广州等。秦桧死,召为吏部郎官,迁右司。因母老,出知婺州。母去世服毕后,除秘书少监,迁权吏部尚书。宋孝宗时因事被迫请求调外,知福州。入朝后,再出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再除吏部尚书,寻兼翰林学士并侍读,又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因谗言连贬秩,气病卧家不起而卒。汪应辰刚方正直,敢言不避。《历代名臣奏议》共收其21道奏章。这些均在《论刑部理寺谳决当分职札子》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五有所节录,并被《历代名臣奏议》所收为全文。
汪奏分三个层次,下面逐一叙述。
第一,宋代审判复核、赦免审核的机构及其运行原理。此层次是对北宋立国以来,所设置的全部审判复核机构、赦免审核机构及其运行原理的综括评价。
国家累圣相授,民之犯于有司者,常恐不得其情,故特致详于听断之初;罚之施于有罪者,常恐未当于理,故复加察于赦宥之际。是以参酌古义,并建官师,上下相维,内外相制,所以防闲考覈者,纤悉委曲,无所不至也。盖在京之狱,曰开封,曰御史,又置纠察司,以纪其失;断其刑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审刑院,以决其平。鞠之与谳者,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有以相济,无独任、偏听之失,此臣所谓“特致详于听断之初”也。至于赦令之行,其有罪者,或叙复,或内徙,或纵释之;其非辜者,则为之湔洗。内则命侍从馆阁之臣,置司详定,而昔之鞠与谳者,皆无预焉;外之益、梓、夔、利,去朝廷远,则付之转运钤辖司,而提点刑狱之官亦无预焉。盖以狱讼之初,既更其手,苟非以持平、强恕为心,则于有罪者或疾恶之太甚,于非辜者或遂非而不改,故分命他官,以尽至公。此臣所谓“复加察于赦宥之际”也。[29]
此层讲了两个问题。
一是“特致详于听断之初”。
汪应辰讲到了北宋前期由太宗和真宗分别创设、被神宗废罢的两个机构:审刑院、纠察司。在南宋,他为什么要讲这两个早已经被废除的机构呢?汪应辰所关注的,是这两个机构的设立所贯穿的精神。
首先,“纠察在京刑狱司”创置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废罢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存在了70余年。纠察司置纠察官二人,以两制以上朝官担任;职责是:“其御史台、开封府,在京应有刑禁之处,并得纠举;逐处断徒以上罪,于供报内未尽理及淹延者,并追取案牍,看详驳奏。”[30]其有两项权利,第一是纠举权,第二是通过“供报”备案而行使的看详驳奏权。后来,对大案重案派员审问,或提到本司录问,则在供报的文字审阅之外,一度又有勘鞫权,之后又下令纠察司不再鞫狱。
汪应辰所说“在京之狱,曰开封,曰御史,又置纠察司,以纪其失”的要点有二:第一,京城监狱不止这两所,“自开封府、御史台、大理寺、诸寺监、开(封)祥(符)二县并尉司、左右外厢、马步军司、三排岸以至临时诏狱,以及昼监夜禁等”[31],共有20多处。其与监狱对应的是审判权,管理监狱者往往同时也是审判机构。因此有了第二点的“以纪其失”,这个“失”包括存在“冤滞”“冤滥”等实体与程序问题。比如“未尽理”可能是“冤”或“冤滥”,“滥”指浮泛、不合实际,同样指断狱冤枉失实的实体冤枉;“淹延”是“滞”,指刑狱未能及时处理而“久系不决”。宋代主张恢复纠察司的吕陶,就讲纠察司的好处在于:“专意于决讼报囚之事”,“求冤抑”“审惨暴”,“刺伺防检,深得其要”,“或留系之淹久,或处决之过滥,大则条奏辨明,小则移文戒督”[32]。纠察司在性质上属于审判监督机构,对冤抑、冤滥属于实体监督,对“淹滞”则属于程序监督。
其次是审刑院。太宗“淳化二年,增置审刑院。知院事一人,以郎官以上至两省充,详议官以京朝官充,掌详谳大理所断案牍而奏之。凡狱具上,先经大理,断谳既定,报审刑,然后知院与详议官定成文草,奏记上中书,中书以奏天子论决”[33]。审刑院属于审判复核机关。本来,宋初大理寺“不复听讯,但掌断天下奏狱”,其只是对地方上报案件进行复核,至此,又须“送审刑院详讫,同署以上于朝”[34]。原来对大理寺奏案进行复核的是刑部,“国初,以刑部覆大辟案”[35],审刑院等于剥夺了刑部职权。
汪应辰奏折中的“鞠之与谳者,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有以相济,无独任、偏听之失,此臣所谓‘特致详于听断之初’也”中的“鞫”与“谳”比周林的“狱司推鞠,法司检断”的狭义的鞫司、法司含义更为广泛,因为纠察司、审刑院不是“检断”的“法司”,相对的那些机构,包括开封府、御史台等以及大理寺、刑部等,也都不是只负责“听”而不予以“断”的“鞫司”。开封府等机构既“鞫”也“谳”,内部实行狭义的“鞫谳分司”,自无问题;而纠察司、审刑院以监督、复核为工作内容,其所谓“谳”,即“请谳”,是动词,含义为上报案情。这样,御史台、开封府等向纠察司“供报”,有“日报”,有“十日一报”,大理寺“狱具”“报审刑(院)”,均为“将案情上报”之义。何况,“审刑院……掌详谳大理所断案牍而奏之”,这反映出其作为广义“谳司”的特征。
因此,汪应辰奏章不能与周林奏章同理解为是针对狭义的“鞫谳分司”,因为他的论证、上下文义都是在广义上使用的。而他所谓的“听断之初”更不是均指初审,有的显然是复审,他只是认为最终定论之前都属于这个阶段。“致详于听断之初”中的“详”指审慎,为达到审慎目的,在普通狱司之外设置纠察司,在大理寺、刑部等复核机构外,又设置审刑院,旧机构与新设机构“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有以相济,无独任、偏听之失”,不独任、不偏听就是他所谓的“特致详于听断之初”。
二是“复加察于赦宥之际”。
史籍中记载了主掌赦宥的官署,中书省八房之一的“刑房,掌行赦宥及贬降、叙复”;六部之一的“刑部,掌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之事”[36],尤其“除雪、叙复、移放,则尚书专领之”[37]。就赦宥内容而言,汪应辰所谓“赦令之行,其有罪者,或叙复,或内徙,或纵释之;其非辜者,则为之湔洗”,即分别相当于这里对官员犯罪的“叙复”“移放”与“除雪”。
有关赦宥程序,史籍中涉及较少。《宋史·刑法志三》述及“恩宥之制”的程序,也比较简单:“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⑨不过,这一记载可以理解为制度或体制,在实行中形成了自己的机制:“畿内则遣使”变成了“内则命侍从馆阁之臣,置司详定,而昔之鞠与谳者,皆无预焉”[38],排除了原来定罪量刑的鞫司与谳司,使用皇帝身边大学士、待制等人开府定夺;“诸路则命监司”形成了“外之益、梓、夔、利,去朝廷远,则付之转运钤辖司,而提点刑狱之官亦无预焉”,排除了原来定罪量刑的提点刑狱司,另外启用无关的转运使。另行择官的运行原理考虑的是:原官员在“狱讼之初,既更其手”,如果不能“以持平、强恕为心”,则一种可能是“于有罪者或疾恶之太甚”,另一种可能“于非辜者或遂非而不改”;“疾恶太甚”必然维持原判决,对罪人不利;“遂非不改”导致见错不纠,对无辜者不利。“故分命他官,以尽至公”,“他官”没有利益和情绪掺杂其中,就能公以处置。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复加察于赦宥之际”。
综上所述,纠察司是从司法系统外部对御史台等中央及京畿司法机构进行复核监督,审刑院也是以一个独立机构的身份从外部监督大理寺、刑部的复核情况。前者是纠驳,从原来御史台职掌分出;后者是“谳”而再“谳”,从原来刑部职掌而得。学士待制等另外“置司”主持赦宥事宜,也具有另立机构的意义。对此,不惜打破现有体制,以新生取代旧有,道理何在?好处何在?汪应辰也给予了归纳,他说:这种“参酌古义,并建官师”的做法,主旨是“上下相维,内外相制,所以防闲考覆者,纤悉委曲,无所不至也”。其中,“并建”官署是真,“古义”是否有这种做法倒是值得推敲;而“相维”“相制”的“防闲考覆”,已是“纤悉委曲,无所不至”。
第二,关于神宗元丰改制中的中央两大法司分职。
迨元丰中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治狱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狱,一以断刑;刑部郎中四人,分为左右,左以详覈,右以叙雪,虽同僚,而异事,犹不失祖宗所以分职之意。本朝比之前世狱刑号为平者,盖其并建官师,所以防闲考覈者,有此具也。[39]
元丰改制,神宗“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40],元丰元年下诏恢复大理寺狱,并同时健全大理寺官员设置,《宋史·刑法志三》所载“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鞫讯;检法官二人,主簿一人”[41];元丰五年,“分命少卿左断刑、右治狱”,形成新格局。所谓“以大理兼治狱事”,实际是恢复其审判权力。同时,刑部郎中、员外郎,在审刑院撤销后,职权回归,四郎官分左右厅,左主详覆,右主叙雪。汪应辰认为,两个大理少卿分管治狱、断刑,四个刑部郎官分掌详覆、叙雪,“虽同僚,而异事,犹不失祖宗所以分职之意”⑩。汪应辰心目中的理想格局是机构分立的分职;现在在同一个机构,是同僚而异事的分职,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分职,也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因而,评价也还是积极的:这种“并建官师”“防闲考覈”的办法,是“本朝比之前世狱刑号为平”的原因。当然,相对于他对太宗审刑院、真宗纠察司的评价“并建官师,上下相维,内外相制”(11)“防闲考覆,纤悉委曲,无所不至”[42]差了几层。
第三,关于南宋中央两大法司的员额、分职问题。
恭惟陛下宽厚慈惠,以祖宗之心为心,其于庶狱丁宁告戒,前后非一。惟是中兴以来,百司庶府,务从简省。大理少卿往往止于一员,则治狱、断刑皆出于一人,则狱之有不得其情者,谁复为之平反乎?刑部郎官或二员,或三员,而关掌职事,初无分异,然则罚之有不当于理者,又将孰使之追改乎?欲望陛下明诏执事,刑部、理寺之官虽未能尽复祖宗之旧,亦当遵用元丰定制。庶几官各有守,人各有见,参而伍之,反复详尽,以称陛下钦恤之意,亦以为后世法。[43]
汪应辰觉得南宋官府精简的结果与两大法司设官颇成问题:大理少卿多是一员,使“治狱、断刑皆出于一人”,原初互相“平反”之职无人履行;刑部郎中、员外郎合起来不过两三人,职掌没分别,原有的分厅治事,一主详覆、一主叙雪的格局不再,互相“追改”错误的机制也无法运行。
有鉴于此,汪应辰建议:当今,刑部、大理寺两大法司,即使恢复不到太宗、真宗时的法度,至少要恢复到神宗元丰制度上;因为,分司的作用,一是使得“官各有守,人各有见”,发挥两个积极性;二是更主要的是,使得分职后的机构之间互相“参而伍之,反复详尽”,通过互相错杂、互相监督,一次再次的审慎机制,达到贯彻司法的最高宗旨——“恤刑”原则。
可见,周林的“鞫谳分司”是狭义的,仅仅针对府州司理与司法参军等;汪应辰虽也有一处涉及狭义“鞫谳分司”,但主要论证提到的“鞫谳分司”是更大视野范围的“分职”大格局。我们在引用时,应加以区别使用,不能以都有“鞫”与“谳”的用字而将两者混淆了。
职此之故,评价也应有所区别。
3.结论的得出与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州府“鞫谳分司”的出现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宋代司理参军、司法参军的职能分化,源于体制上的新生与旧制并存状况。为了不叠床架屋而不得不分工,故其出现是偶然的;而职能分化后的互相掣肘的情态促使对当时这一制度的存在道理进行挖掘,寻找其合理性、必要性,其出现又是必然的。周林的意见就是证明。
其次,汪应辰的大范围的分职评价,可以借用来分析狭义的“鞫谳分司”。
比如,纠察司纠正开封、御史狱,审刑院复核大理、刑部判断,使得体制上和运作上“无独任、偏听之失”,对新设机构在功能上避免“独任”“偏听”,可以借用来评价司理、司法参军之间“鞫谳分司”的优点。
又如,“更手”官吏及其机构“无预”赦宥之事,而是“分命他官,以尽至公”,可以用来评价大理、州府的狭义“鞫谳分司”,因为他们在本质上也是“分命”以达“至公”的;尤其其间的心理分析,有一定道理。
再如“同僚而异事”,“不失祖宗所以分职之意”,是综合大理、刑部分职而提出的,我们除了用其评价大理寺左断刑、右治狱的狭义“鞫谳分司”外,当然可以借用其来评价府州司理与司法参军的“鞫谳分司”,即司理与司法参军等也是“同僚而异事”以“防闲考覈”的。
对“鞫谳分司”,宋人评价以及我们的分析已如上述。看重广义的分职,是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狭义“鞫谳分司”。那么,宋人在狭义“鞫谳分司”上做得如何?我以为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则,规定与要求几近苛刻。
不“独任”而分司执事,在当时制度约束上,严厉禁止鞫司与谳司接触。一是禁止谳司与鞫司官员、吏胥见面:“诸被差鞫狱、录问、检法官吏(并谓罢本职、本役者),事未毕与监司及置司所在官吏相见,或录问、检法与鞫狱官吏相见者,各杖八十。即受置司所在供馈,并与者,各加二等(所鞫事不相干者,事毕听受)。”[44]禁止见面,主要是担心鞫司与谳司商议案情,影响审讯和检法拟判。正如前述,先是对检法吏人,后来是对整个检法司的禁约,“应检法者,其检法之司唯得检出事状,不得辄言与夺”[45]。
二则,当时有人对“鞫谳分司”存在着过于理想化的期待,以致于提出了难说是合理的要求,估计其难以实现。
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有臣僚上言指出当时“治狱之弊”并提出了革除办法,涉及了鞫司和谳司两方面。
关于鞫司,“今日治狱之弊,推鞫之初虽得其情,至穿款之际,则必先自揣摩斟酌之,以为‘案如某罪’‘当合某法’,……必欲以款之情与法意合”(12)。这个指责是希望“鞫司”不要附于刑、丽于法——因为那是谳司的工作。遂建议朝廷“行下诸路州军,所隶刑狱应自今圆结案款,但据其所吐实辞,明白条具,然后听其议法者定罪。不得仍前傅会牵合,稍有文饰”[46]。
但这个禁令难以真正落实。“案如某罪、当合某法”[47],作为审讯者对案情熟悉后的推断,必然会在他头脑中形成,禁止是禁不掉的。
对于上述禁令,臣僚希望鞫谳二司“如有违戾,监司按法施行。庶几情得其实,法当其罪”(13)皇帝“从之”,采纳了这个建议。
在机制上,希望杜绝鞫司与谳司之间互相揣摩、互相迁就,期待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并不现实,也难以存在。
总之,宋朝“事为之防,曲为之制”(14),诸事预先做防范,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遂有了分职、分权原则,从机构和功能两方面,建立起以司法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及外部制约机制的“鞫谳分司”制度。在这过程中,形成了价值阐释,出现了花样翻新的落实制度、实现机制。至于它的前途和命运,纠察司、审刑院等一时兴起、过时废罢的制度,自不必说;大理寺、刑部在明清时期发生了机构性质的重大改变,也不消说;即如府州“鞫谳分司”制,元代没有沿用,明清也不见痕迹,其原因可能是:司理参军与司法参军的分工、掣肘之说,是新旧两个机构并立之后的衍生物。司理参军的存在,与司法参军在职能上形成叠床架屋,既然并存,就不得不有分工。但司理参军的出现是一种偶然。它之出于机构或人群之间互相掣肘的体制考虑,是引申出来的。毕竟只能兴于一时,一旦当时顾虑的原因或条件丧失——改造武人掌握的马步院为司理院——制度设计的理由不存在或弱化了,制度也就容易归于消灭。但它在司法制度发展史上的探索和贡献——“听(审)”“断(判)”所具有的不同价值追求,却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它尤其能引起我们的思考。
比如,把对疑案的驳正权赋予司法参军,是否合理?是否责任太大?因为司法参军没有参加鞫问,不符合当今所谓的司法的亲历性原则,让其驳正疑窦,岂非强人所难?合理性的考虑则在于:疑窦是根据常识来进行的,并不难操作;而且他审查的是证据,对象明确;好处还在于:他是审讯的局外人,没有先见,所以可以一眼看出问题,如此等等。
作者简介:
霍存福,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沈阳 110034;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12
注释:
①《宋会要辑稿·刑法》内容参见陈景良:《宋代司法传统的现代解读》,《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
②《攻媿集》卷98《中书舍人赠光禄大夫陈公神道碑》。转引自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3页。
③《宋会要辑稿·刑法》相关内容。转引自陈景良:《宋代司法传统的现代解读》,《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
④《宋史·罗必元传》转引自张湘涛主编:《名人张沙风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⑤以上两个案例转引自魏文超:《宋代证据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⑥《折狱龟鉴》相关内容转引自陈霞村:《文白对照断案智谋全书》,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06-408页。
⑦转引自[明]郭棐:《粤大记·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5页。
⑧[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49页,文中所述有关于周林之事亦见于此。
⑨转引自王忠灿:《“狱”“狱空”和中国古代司代传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0页。
⑩转引自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3·隋唐五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8页。
(11)《宋会要辑稿·刑法》相关内容转引自陈景良:《讼学与讼师:宋代司法传统的诠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5-226页。
(12)《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五十九转引自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76页。
(13)《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五十九转引自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76页。
(14)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即位诏书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一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82页。
原文参考文献:
[1][6]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282-283页。
[2]《庆元条法事类》卷73《刑狱门三·出入罪·旁照法》,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755页。
[3][10][17]《庆元条法事类》卷73《刑狱门三·推驳·格·赏格·命官》,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758、758、757-758页。
[4][7][8][9][16][18][19][20]《庆元条法事类》卷73《刑狱门三·推驳·令·赏令》,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756、756-757、756-757、756、757、756、756、756页。
[5][11]《庆元条法事类》卷73《刑狱门三·推驳·断狱敕》,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756、756页。
[12]《庆元条法事类》卷73《刑狱门三·推驳·式·赏式·保明推正驳正入人死罪酬赏状》,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758页。
[13]《庆元条法事类》卷73《刑狱门三·出入罪·令·断狱令》,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755页。
[14][15]《庆元条法事类》卷73《刑狱门三·出入罪·旁照法·断狱敕》,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755、752页。
[21]《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户婚门·归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4-225页。
[22][23]《宋史》卷119《职官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467页。
[24]《折狱龟鉴》卷8《矜谨·李应言按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13页。
[25][34]《宋史》卷118《职官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443、2441页。
[26]《宋史》卷164《职官司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679页。
[27][28][39][43]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17《慎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三册,第2850、2850、2850、2850页。
[29][33][35]《宋史》卷164《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679、1679、1679页。
[30]《宋大诏令集》卷161《置纠察在京刑狱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10页。
[31][32]《净德籍》卷2《奏为乞复置纠察在京刑狱司并审刑院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98册,第16、16页。
[36][37]门岿主编:《工州四史精要辞典》,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1740、1740页。
[38]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17页。
[40]《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82《大理寺狱》,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57页。
[41]《宋史》卷154《刑法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51页。
[42]《历代名臣奏议》卷217《右司郎中汪应辰论刑部理寺谳决当分职札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52-2853页。
[44]《庆元条法事类》卷9《职制门六·馈送·断狱敕》,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168页。
[45]《庆元条法事类》卷73《刑狱门三·检断·断狱令》,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742页。
[46]郑寿彭:《宋代开封府研究》,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0年,第776页。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