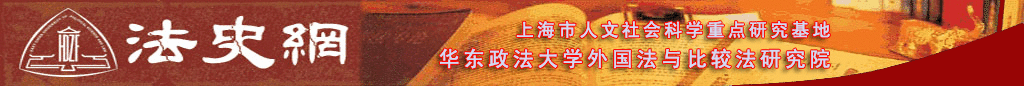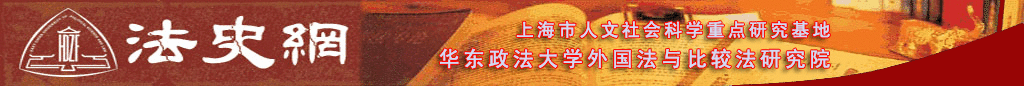【中文关键词】 神明裁判;宗教信仰;诉讼证据;幕府
【摘要】 神明裁判是古代司法证据制度不发达的产物,当司法官员对于原、被告双方的是非曲直难以判明时,便借助于神意来裁判、。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审判方式,是基于人们对原始宗教的崇拜和对自然界的无知认识而产生的。中日两国在古代法制文明初期,都有过占卜裁判的情况,后来随着两国律令法体系的建立,有效地解决了疑难案件证据不足的问题,使神明裁判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从公元13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日本幕府统治的确立,儒家“无讼是求”的观念和日本法律处于秘密的状态,严重制约了诉讼审判制度的发展,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出现了神明裁判复活的迹象。
【全文】
在司法证据制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当审判人员对原、被告双方的是非曲直难以判明时,往往借助于神意来审查证据和裁判案件,这就是所谓的神明裁判。神明裁判制度是古代证据制度和司法鉴定技术不发达的产物,是基于人们对于鬼神的崇拜和对自然界现象的无知认识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而产生的,没有任何科学性和合理性可言。古老的神明裁判方式在世界许多国家进入到文明社会之初长期施行,自然有其存在的法律土壤,它对提供虚假证据的犯罪嫌疑人能够在心理上给予一定的威慑,在人类法律文明早期的司法实践领域广为流行,几乎成为世界各民族法律文明初期的一种共性,因而一直是法律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当人类一旦摆脱了对神灵的盲目崇拜后,神明裁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
神明裁判是人类法律史上最古老、适用范围最广泛、实施时间最长的一种审判方式。关于神明裁判的起源,有些学者认为可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1]由于当时的私有观念不发达,神明裁判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有盟诅、占卜等形式。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国家的出现,神明裁判的方式不断增多,一些野蛮的神判方式相继出现,如沸水神判、毒蛇神判等成为古代世界各国早期重要的裁判形式。
世界古代各国的神明裁判类型很多,日本学者穗积陈重把神明裁判分为讯宣和神裁两种类型,他指出:“讬宣者,争讼有嫌疑时,当事者或审判官,就僧侣、巫祝、卜者等之神意感通者,请神示其曲直,依之而下判断,此神意之启示,谓之神讬;神裁者,当争讼有疑难时,请神示其曲直,以奇迹之示显,为神意裁判。”[2]目前国内外法学界通常把神明裁判分为两大类:其一,神誓盟诅。具体的方法是,当原、被告就案件的事实提出相互矛盾的陈述时,审判官或诉讼双方的调解人以及原、被告一方提出向神宣誓,以保证其陈述的真实性。假如有另一方不敢对神宣誓盟诅,或者在宣誓后呈现出某种灾异谴告或报应的现象,便判定其陈述虚假。其二,神意裁判。神意裁判是在诉讼过程中以某种方式请求神示意裁决的方式,原、被告双方通常要经过肉体的考验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神明裁判是古代证据制度和司法勘验技术不发达的产物,对于请求伸张正义的诉讼一方来说是不公平的,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和证据学理论的不断发展,神明裁判制度最终被世界各国的法律所摒弃。
古代东西方法律史上都有过神明裁判的记述。据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法典》记述:“引诱自由民之女离家外出,而女之父母知之者,则引诱此女之人应对神发誓云:‘彼实知情,过应在彼’。”[3]这是典型的神誓立证法。古代欧洲的日尔曼法中,也长期实行神明裁判,美国学者孟罗•斯密(EdmundMunroe Smich)在《欧陆法律发达史》一书中,对日尔曼人的神誓、神判作了如下论述:“既然在当时以为惟‘神’始能知是非曲直,故关于争端之解决,不外采用下列二种方法之一,或用某种足使神得藉以指明是非曲直之方法,如神判(ordeal)方法是;或用一种心理强制之方法,诉诸一方当事者之恐怖心,使之觉得如其故作虚伪,势将触犯神怒,因而不能不为真实之陈述。”[4]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也谈到了古代日尔曼人的神明裁判方式:“在被告把手放在热铁上或插进开水里之后,人们就把他的手用一个口袋包裹起来,加上封印。如果三天后没有烧伤的痕迹的话,就把这人宣告无罪。”[5]
古代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都曾施行过神明裁判。古代的中国和日本与古代欧洲又有所不同,在公元9世纪,欧洲的法兰克王国率先规定在涉及王室利益的案件中不再使用神明裁判的方式。在公元12世纪英国亨利二世(Henry II)时期,当时的司法审判也很少采取神明裁判的方法。公元121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认为神判与基督教的教义相违背,禁止教士参与神明裁判。从此,神明裁判的方法在欧洲大陆很快绝迹,再也没有复活。而古代东亚的中国和日木则有所不同,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律令法体系的确立,在民事法律活动中注重书证、物证和人证,采取了书证优先的原则,使古老的神明裁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古代日本在公元7世纪中叶后,全面受容唐代的律令法体制,神明裁判的方式一度废绝。但是,在中国古代后期的元明清三代,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司法制度的僵化,加之疑罪收赎制度的废除和司法官员法律素质的低下,许多地方司法机关对于疑难案件又采取了神明裁判的方式。古代日本在镰仓幕府以后,随着武家专权局面的形成和原始宗教神道教的复兴,出现了同态复仇和私刑主义的观念,[6]法律的神秘色彩浓厚,大化改新之后确立的律令制的审判模式遭到了严重破坏,神明裁判在日本很多地方又复活了。从公元13世纪镰仓幕府到江户幕府时期,神明裁判广泛适用于日本的民事、刑事诉讼审判活动中,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加以废除。
中日两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交流十分密切,两国古代的法律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中日两国古代的神明裁判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国内外法史学界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古代神明裁判制度作了认真细致的研究,也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光中的《古代的神明裁判》,[7]夏之乾的《神判》,[8]杜文中的《神判与早期习惯法—兼及中西法律文化传统比较的一个侧面》,[9]吴海航的《日本古代神判法探析》等。[10]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田薰的《古代亚细亚诸邦に行はれたる神判》、《古代亚细亚诸邦に行はれたる神判捕考》、《起请文雜考》等系列论文,[11]仁井田陞的《民简信仰と神判》,[12]曾我部静雄的《关于探汤》,[13]牧野信之助的《关于神誓裁判》,[14]伊藤清司的《铁火神判系谱杂记》[15]等。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学者对中日两国古代的神明裁判制度进行比较。中日两国古代都曾长期施行神明裁判,其实行神明裁判的原因是什么?中日两国古代神明裁判的方式有何不同?为什么在中日两国古代社会后期又出现了神明裁判复活的迹象?神明裁判对中日两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上述这些问题,很少有学者进行专门论及。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对中日两国古代的神明裁判制度进行比较,不妥之处,请求指正。
一、中日两国古代实行神明裁判的原因比较
神明裁判制度是古代证据制度不发达的产物。当人们对某一案件的真相不能判明时,便借助于神意来确定是非曲直。神明裁判并不科学合理,其所以能够在远古时代为世界许多民族所认同,自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古代许多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上都曾施行过神明裁判,说明神明裁判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生活禁忌、政治制度和法律文明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神明裁判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初期为了解决证据不足而出现的依靠神意裁判解决纠纷的一种审判模式,是一种非理性的审判方式,也是人类法律文明初期最原始的审判方式。世界许多文明古国如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以及欧洲的日尔曼蛮族国家等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实行神明裁判。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和法制文明的发展,其缺乏理性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神明裁判渐渐失去了神秘的光环,为人们所摒弃,依靠神意裁判的方式逐渐为证据决定论所取代。新型的审判方式注重书证、物证和人证,依靠证据来判明是非,这种审判模式与依靠虚无飘渺的神意裁判相比,无疑具有进步性,也更能为人们所接受。古代欧洲从12世纪以后逐渐废除了神明裁判。当神明裁判制度一旦被废除,就很难再能复活。
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例外的现象,例如有些国家和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初期施行过神明裁判,后来一度废止,但经过一段时期后又加以复活。古代的中国和日本便属于这种情况。纵观古代中日两国神明裁判的发展轨迹,有很多相似之处。古代东亚地区的中国和日本在律令制的法律体系确立之后,神明裁判的方式一度废绝。但到了中国古代后期的元、明、清三代和日本幕府时期以后,随着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强和司法体制的僵化,许多地方又出现了神明裁判的方式。神明裁判在古代中国和日本长期施行,其原因是什么?许多学者都发表过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受宗教因素的影响和司法制度的严重倒退。
(一)中日两国的神明裁判都与本国的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神明裁判与该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在世界古代,几乎所有民族都有信奉宗教的历史,而宗教信仰又与神明裁判有密切的关系。日本学者穗积陈重指出:“在信神心最深之社会,一般人民,信神之全知全能而畏敬之,欺神者必受惩罚,故古代多以宣誓为判断诉之曲直、罪之有无为最确实之方法。”[16]美国学者哈罗德•J.伯尔曼也认为,欧洲信奉的基督教支持了神明裁判和共誓涤罪裁判的日耳曼法律制度,当时的人们通常会认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上帝参与审判,能客观公正地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神明裁判很正式,由神父主持仪式,被告人在参加弥撒仪式之前必须向神父坦白。如果被告人有罪,在陈述的过程中隐藏罪行,在神父做弥撒时被告人接受了圣礼,被认为是犯了使灵魂死亡的罪恶。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当罪犯不能承受的时候,便坦白自己的罪行。弥撒之后,神父祈求神的指导,然后开始神明裁判。[17]
中国古代是一个多神的国度,但主要是对天帝和鬼神的信仰。《吕氏春秋•顺民》说:“天神曰神,人神曰鬼。”早在夏商周时期,已有对天帝、鬼神的崇拜,夏商两代的统治者宣称“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殷人迷信天命鬼神,已为传世的古代文献资料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所证实。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日本民族对天地神祗的信仰由来已久。据《日本纪略•前篇三》“崇神天皇”条记述,崇神天皇六年,因百姓流离,或有背叛,乃请罪神抵。“先是,天照大神,倭大国魂二神,祭于天皇大殿之内。”这里的“请罪神抵”,显然是神判的一种方式。在公元1世纪至7世纪,日本社会原始宗教、咒术盛行。日本古代的“罪”字,其含义不仅包括破坏田畦、毁坏水利设施等行为,也含有高津神灾(雷灾)、胡久美(瘤症灾)等天灾的意思,“罪”字也有天罚的含义,即由于人为的因素,招致神怒,天神降罪人间。
中日两国的神明裁判都受到过佛教信仰的影响。众所周知,佛教宣扬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的理论,要求人们生前做善事,不说妄语,否则死后会遭到报应。在佛教的戒律《四分律》中,就有佛教徒不得说妄语的规定。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后,迅速在民间社会传播开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信仰阶层,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也为广大的佛教徒所接受,若有人不遵守诺言,就会遭到报应。据《太平广记》卷434引《法苑珠林》记述,唐永徽年间,汾州义县人路伯达,负同县人钱一千文。后共钱主佛前为誓说:“我若未还公,吾死后,与公家作牛畜。”这说明在古代民间发生债权债务纠纷时,常常采取在佛像前盟诅的方式。在佛教的世界中,还虚构出了一幅地域审判的谱系,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佛说十王经》中,描绘了阎王、判官审讯世间各种作恶之人的场景。[18]
公元6世纪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也为日本古代民众所信仰。到平安时期,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佛教宗派是禅宗,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成佛速成论,使佛教在日本社会迅速传播开来,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下层百姓,都热心参禅。日本高僧最澄、空海等人以镇护国家为宗旨,提倡“为国忠,在家孝”,“为国念颂,为国祈祷,为国讲《般若》”,把佛教与日本的原始神道信仰相结合。到9世纪初,在越前的气比神宫、伊势的大神宫、尾张的热田神宫等都建造了神宫寺,在八幡神宫内出现了佛教的菩萨。据八幡神名“御讬宣”记载:“得道来不动法性,示八正道垂榷迹,皆得解脱苦众生,故号八幡大菩萨。”[19]
佛教对日本古代的神明裁判产生了重要影响,幕府时期许多神判经常在佛寺和神社进行,盟誓中也掺杂着诸神佛教的内容。[20]据《高野山文书》卷七记载:“神罚冥罚于沙弥法莲身上八万四千毛孔,今生受白癫黑癫重病,来世堕无间狱不可有出期。”可见,日本的神判和天罚是受到佛教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观念的影响。
(二)不同的宗教信仰对中日两国神明裁判的形式产生了直接影响
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道教,道教的神仙谱系很多,有传说中的玉皇大帝、西王母等人们虚构的神仙系统;有民间广为颂扬的英雄人物如关圣帝君、三界圣神等;有为人们带来福祉的城隍、土地、灶神、药王等;有基于人们对自然界的某些现象认识模糊而产生的自然神,如风神、雨神、雷神等;还有人们畏惧的瘟神、蛇神等。古人认为神是无所不能的主宰,具有辨别善恶是非、赏贤罚暴的能力。。战国时期的墨子认为:“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21]
中国古代民间借助于城隍、关圣帝、三界神、温元帅神等信奉的鬼神进行神明裁判的事例很多。元朝大德二年(1298年),田滋在任浙西廉访使期间,有县尹张或被诬以赃,“狱成,滋审之,但俛首泣而不语。滋以为疑,明日斋浴,诣城隍祠祷日:‘张或坐事有冤状,愿神相滋,明其诬。’守庙道士进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状到祠焚祷,火未尽而去之,烬中得其遗稿,今藏于壁间,岂其人耶?’视之,果然。明日,诣县司诘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状示之,皆惊愕伏辜。张或得释”。[22]明清之际,广东地区信奉三界神,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6记述了当地民众向三界神乞蛇神判之事:“广有三界神者,人有争斗,多向三界神乞蛇,以决曲直。蛇所向作咬人势则曲,背则直。或以香花钱米,迎蛇至家,囊蛇探之,曲侧蛇咬其指,直侧已。”
古代日本的原始宗教是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民众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号称有八十万神或一千五百万神,其中特别崇拜的是太阳神和皇祖神合一的天照大神。据《养老令•神祗令》记述,民众信奉的神有天照大神、地神、疫神、风神等。[23]古代日本的神道最初缺乏宗教理论基础,到镰仓、德川幕府时期,一些神道学者把神道的教义、中国的朱子学和佛教思想加以整合,完善了日本的神道理论体系。古代日本的神明裁判与民众的神道信仰有密切的关系,神判所恭请的神多为日本原始宗教所崇信的神,裁判的地点大多选择在神社进行。据《吾妻镜》卷30“嘉祯元年(1235年)闰六月廿八日”条记载:“今日被定起请失之篇目,所谓鼻血出事,书起请文后病事(但除本病者),鵄乌矢悬事,为鼠被衣裳事,自身中令下血事,重轻服事,父子罪科出来事,饮食时咽(但被打背之程,可定失者)、乘用马毙事。已上就个条,是于政道以无私为先,而论事有疑,决是非无论,故仰神道之冥虑,可被乣犯否云云。”
总之,古代的中国和日本社会都有对自然神和鬼神的崇拜。后来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的朱子学和佛教传入到日本,使两国古代的诉讼审判制度有许多相似的特征。但是,由于中日两国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两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不同,中国的本土宗教是道教,日本民众信仰的宗教是神道教,受不同宗教文化的影响,中日两国古代的神明裁判又有明显的差异。
二、中日两国古代神明裁判的方法比较
世界古代各国的神明裁判方式很多,有水审、火审、毒审、食审、触审、斗审等不同形式。有些学者把古代世界众多的神明裁判分为单审神裁法和对审神裁法两大类。[24]但无论如何划分,神明裁判都是人们借助于神意来明辨是非的一种审判方式。
古代中日两国在法律文明初期都施行过神明裁判,神明裁判的方式也很单一,主要是占卜神判。随着中日两国律令制法律体系的衰落,在中国元明清三代,当某些司法官员面对疑难案件无法判明时,又采取了神明裁判的方式。古代日本从镰仓幕府以后,司法制度发生了重要转型,原来律令制下的诉讼审判模式遭到破坏,武家制定的法律文件《贞永式目》、《建武式目》、《武家诸法度》、《公事方御定书》等成为最重要的法律,原来的律、令、格、式成为补充法,大部分变成了死法,日本法律进入到以习惯和常理为主的不成文法时代。[25]据《吾妻镜》记载,建长五年(1253)二月,关于儿童之间以刃伤人在《贞永式目》中未有规定,当时的明法家提出了“式目之外守法意”的判决意见。[26]在幕府统治时期,由于武家专权局面的形成,日本的诉讼审判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倒退,许多地方又出现了神明裁判的现象。
古代中日两国的神明裁判方式有相类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总体来看,日本幕府时期神明裁判所适用的范围比中国广泛,神明裁判的种类也比中国多。而在中国明清时期,司法机关所采取的神明裁判方式只是极少数的个案现象。
(一)古代中日两国神明裁判的方式比较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述,中国和日本古代的神判方式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有通过占卜的方式进行裁判的情况。据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记述,中国上古时期,商代占卜神判盛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多次出现通过占卜的形式定罪量刑,有些学者将其称为“卜筮决狱”。甲骨卜辞表明,对犯罪者定什么罪,处何种刑罚,贞人都要在神前卜问,然后按照卜兆,立即行刑。[27]两汉时期也有卜筮裁判的情况,据《史记》卷127《日者列传》记载:“(孝武帝时)辨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无行为主’。”这里的“辨讼不决,以状闻”,即是典型的占卜裁判。
古代日本也有占卜裁判的情况,据《后汉书》卷85《东夷传》记载,倭人迷信卜筮,每遇难事,则“灼骨以卜,用决吉凶。”《隋书》卷81《倭国传》也记述:“(其俗)知卜筮,尤信巫觋。”日本古代文献《日本书纪》中,明确记述了占卜问罪的事例:“(允恭天皇)廿四年夏六月,御膳羹汁凝以作冰。天皇异之,卜其所由。卜者曰:‘有内乱。盖亲亲相奸乎?’时有人曰木梨轻太子奸同母妹轻大娘皇女,因以推问焉。辞既实也,太子是为储君,不得罪,则流轻大娘皇女于伊豫。”[28]
古代中日两国都有神誓法,神誓法又称神誓立证法,是基于人们认为神能够维护正义、惩罚非正义的信念的一种审判方式,其主要功能是审查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宣誓者向神宣誓后,若不遵守誓言,会在不久的将来遭到神的谴告和报应。中国古代的神誓法通常表现为盟诅,据《周礼•秋官•司盟》记述:“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凡盟诅,各以其地域之众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则为司盟共祈酒脯。”贾公彦注疏说:“谓将来讼者,先使之盟诅,盟诅不信,自然不敢狱讼,所以省事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凡因事实不清而发生诉讼,先让原、被告双方盟诅,如果有一方不诚信,自然不敢进行诉讼。中国明清两代的神誓法案例很多,据《泰泉乡礼》卷5“乡社”条记述:“若乡老听一乡之讼,户婚、田土、财货、交易等情,不肯输服,与社仓出纳保甲疑难之类,皆要质于社而誓之。凡誓鸣鼓七声,社祝唱跪,誓者皆跪,社祝宣誓,词曰:‘某人为某事,某有某情,敬誓于神,甘受天殃遭瘟,招祸凶于其身,覆宗绝嗣,灭其家门,惟神其照察之。’誓毕,誓者三顿首而退。”宣誓人在神灵面前宣读重誓,如果说谎者承受不住心理的压力,便承认过错,使案情得以解决。
古代日本很早就有神誓法。在大化改新之初,日本天皇与皇族在“大槻树下”举行大盟会,向天地神抵盟誓:“天覆地载,帝道唯一,而末代浇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于我,诛殄暴逆,今共沥心血,而自今以后,君无二政,臣无贰朝。若贰此盟,天灾地妖,鬼诛人伐,皎如日月也。”从镰仓到江户幕府时期,神誓法颇为流行,具体的方法是:凡裁判,先由诉讼人即原、被告双方提出证文。若证文证人,俱不分明时,则使双方同具起请文,在神祗前盟誓,宣誓自己所言真实,如有虚伪,甘愿接受神祗的惩罚。据《吾妻镜》卷27“宽喜二年(1230年)五月”条记述:“去夜盗人事,殊被惊愤之故也。于侍召集自去夜参候之辈被纠弹,其中恪勤一人,美女一人有疑殆兮。仍参笼于鹤冈神宫,可书进起请文之由,被仰含毕。”
古代中国和日本都有毒审的记述。中国明清时期,南方某些地区有毒蛇裁判的案例,据清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6记述:“广有三界神者,人有争斗,多向三界神乞蛇,以决曲直。蛇所向作咬人势则曲,背则直。或以香花钱米,迎蛇至家,囊蛇探之,曲侧蛇咬其指,直侧已。”
古代日本是否存在毒审,日本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在中国的《隋书》卷81《东夷传》中有如下记述:“每讯狱讼,不承引者,以木压膝,或张强弓,以弦锯其项。……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蛰手矣。”[29]日本学者藤泽卫彦所著的《日本刑罚风俗图史》一书中,收录了公元12世纪判处“蛇刑”的情况:加贺宰相被传藏和浅尾合谋害死,事发后,传藏被处以“钉牢”刑,浅尾则被处以“蛇刑”。行刑者把浅尾裸体扔到一个很深的坑穴中,然后倒人大大小小的无数条毒蛇,毒蛇或啮咬浅尾的皮肉,或钻入其体内吞食内脏,最后浅尾浑身是血,发疯而死。[30]
古代中国和日本的神明裁判方式也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古代的神判方式主要有触审、毒审、占卜裁判、沸油神判等形式,神判的方式较为单一。古代日本在早期的固有法阶段神明裁判的方式与中国大体类似,但从镰仓幕府以后,随着武人专权局面的形成和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神明裁判适用的范围非常广泛,神判的种类也很多,与中国明清时期的神明裁判相比,有明显的差异。
中国古代最古老的神明裁判方式是触审,裁判的方法是由神兽獬豸或神羊进行裁决。传说在尧舜禹时期,法官皋陶就利用神兽解廌裁判,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解廌者,一角羊,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对于证据不明的疑难案件也采取神羊裁判的方式,据《墨子•明鬼(下)》记载:“昔者齐庄公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在日本古代的文献中,未见有触审的裁判方式。
日本古代盟神探汤的审判方式颇为流行,盟神探汤也称为誓汤。所谓盟神,指向神宣誓,有些学者将其称为宗教的告白过程,类似中国古代的盟诅。向神宣誓,首先要相信神,信仰神灵,对神的裁决深信不疑。为了恭迎神来主持裁决,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须预先斋戒。盟神以后,接下来的程序是探汤,为了表示对神的尊崇,在探汤之前,原、被告双方先洗手、洗口,然后将濡湿的手伸人煮沸的水中取物。古代日本文献记述盟神探汤的事例很多,据《日本书纪》卷10“应神天皇九年(278年)”条记载:天皇任命武内宿弥于筑紫监察百姓,其弟甘美内宿弥妒之,欲废兄自立,乃进谗言于天皇。双方争执激烈,天皇推问二人,是非难决。最后天皇下敕旨,“令请神抵探汤,是以武内宿弥与甘美内宿弥共出于矶城川湄为探汤。武内宿弥胜之”。在继体天皇二十四年(530年)九月,任那的毛野臣滥用职权,凡遇到民间争讼,每每施以盟神探汤,民众苦甚。[31]这说明在大化改新以前,盟神探汤的裁判方式经常被用于司法审判之中。
中国古代汉族政权的司法审判中没有盟神探汤的方式,但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有沸捞神判的事例。在《南昭野史》卷下记述了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沸捞裁判的情况:凡“有争者,告天,沸汤投物,以手捉之,曲则糜烂,直者无恙”。明清时期,南方一些偏僻的地区有捞油裁判的形式,据《续新齐谐》卷1“受私桥”条记载,李某借其友张某钱若干,张向李索取,李拒不承认。张忿曰:“汝明日若敢赴城隍庙盟誓摸钱,吾即休矣。”李应喏。该乡人信鬼神,相传城隍神最灵,“神前煎油锅,置钱中,理直者手摸不烂,否则必烂。”翌日,张李二人同往城隍庙,“撞钟鼓陈颠末,然后置钱铛熬沸油,掷一钱于油中,令人手摸,李竟取出,而手无恙。于是众咸非张,张亦不能再辩。”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有用鸡占卜裁判的事例。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述:“鸡卜,南人占法,以雄鸡雏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扑鸡杀之,拔两股骨,净洗,线束之,以竹筵插束处,使两骨相背于筵端,执竹再祝。左骨为侬,我也。右骨为人,人,所占事也。”在日本的古代文献中,未见有用鸡占卜裁判的现象。
古代日本幕府时期,铁火裁判十分流行。铁火裁判又称火起请,具体的方法是:先将起请文放于手掌,然后在上面放上烧红的铁块,若没有烧伤,无罪;反之有罪。室町幕府至江户幕府时期,许多文献都记有铁火裁判的事例。文禄四年(1595年),在肥前的大村,因某基督教徒有偷盗嫌疑而被判以铁火神判,审判的结果是被告人没有被烧伤,证明无罪。另据《玉露丛》记述,庆长十九年(1614年),在骏河国(静冈县)的熊野森,对有杀兄嫌疑的弟弟施以铁火神判,江户幕府的重臣彦坂光政亲临现场监督。为了表示公正,主持人有时会让双方交换铁斧,被灼伤者如不堪忍受,则被判败诉。中国古代文献未见有铁火裁判的情况。
日本古代有落书起请和无名入文的神判方式。在镰仓中叶以后,日本兴起了一种新的审判方式落书起请。该审判方式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神判,但由于在落书中有“天罚起请文事”的字样,有些学者也将其视为一种神判的方式。[32]从落书的内容看,“落书起请”类似于古代的盟诅。不过“落书起请”的过程又与神誓法不同,它只是神判的初始阶段,接下来的程序是“无名人文”,即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决定犯罪嫌疑人。据《碧山日录》卷3“宽正二年(1461年)三月廿二日”条记载:“南禅寺近日有僧为党,火结雠者所居,源相公(将军足利义政)聆之,欲捕囚其徒而不知之。仍命大众于土地祠前,俾署为恶者名,以其多为验也。名之为无名之判也。”“无名人文”实际上是在神社前通过匿名调查的方式来确定犯罪嫌疑人,故名曰“无名之判。”日本的落书起请和无名入文的裁判方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没有出现。
日本古代还有抓阄的裁判方式,但幕府时期采用抓阉神判的情况并不多。据《亲长卿记》“文明六年(1474年)六月廿九日”条记载:“次仰云此事可为如何哉?劝修寺大纳言、广桥大纳言,予等可申所存云云。就今度相论事被寻仰一社之处,两样申状也。犹以难决殊载罚文之上者,各虽不可有虚言,社司氏人等两样之申状不审事也。所诠凡虑难计事,于神前以御阄子可被决欤?殊旧院之御时,就御不审事,被取御阄子了,可为如何哉云云。”通过抓阉的方式来确认犯罪嫌疑人是非常荒诞的,它不利于司法机关弄清案件的真相,也没有任何公正合理可言。
(二)中日古代神明裁判的地点、参加人员之比较
古代神明裁判为了体现判决的公平性,对神判的地点和参加人员都有明确的要求。古代中日两国神判的地点通常选择在寺庙和神社进行,寺庙和神社被认为是神居住的场所,在神社裁判更能为原、被告双方所接受。参加神明裁判的人员除原、被告双方外,还有司法官员、神职人员、当事人亲属以及邻里等。
中国古代神明裁判的地点大多选择在寺院、城隍庙、山神庙等地。元大德二年(1298年),田滋任浙西廉访使,有县尹张或被诬以赃,田滋选择在城隍祠,说:“张或坐事有冤状,愿神相滋,明其诬。”[33]元至正年间,刘秉直为卫辉路总管,时“贼劫汲县民张聚钞一千二百锭而杀之,贼不获,秉直具词致祷城隍祠,而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莲者,战怖仆地,具言贼之姓名及所在,乃命袭之,果得贼于汴,遂正其罪。”[34]
古代日本神判的地点通常也在寺院、神社进行。据《看闻日记》“永享八年(1437)五月十九日”条记载:“抑山前百姓与观音寺百姓,今日被书汤起请,于成佛寺书之,奉行饭尾肥前同大和以下四五人检知,定直同检知。两方取孔子,当方百姓取之,愿阿(山前古老百姓也)先书起请烧灰吞之,次沸汤之中取石。”另据《碧山日录》卷3“宽正二年(1461年)三月廿二日”条记述:“南禅寺近日有僧为党,火结雠者所居,源相公(将军足利义政)聆之,欲捕囚其徒而不知之。仍命大众于土地祠前,俾署为恶者名,以其多为验也。”上述两次神明裁判的地点选择在成佛寺和土地祠进行。
古代中日两国参加神明裁判的人员略有不同。中国古代参加神明裁判的人员主要有司法官员和双方当事人,神职人员很少参加。当原、被告双方向官府提出诉讼时,司法官员因无书证、人证和物证,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便借助于神意裁判,选择的地点在寺庙或神社,能为原、被告双方所信服。在神判的过程中,司法官员居于主导作用。元朝时,彰德有一富商任甲,出行至睢阳,驴死,令郄乙剖之,任以怒殴郄,经俗而死。郄有妻王氏、妾孙氏,孙诉于官,官吏纳任贿,谓郄非伤死,反抵孙罪,置之狱。王来诉冤,观音奴立即释放孙出狱,呼府胥吏说:“吾为文具香币,若为吾以郄事祷诸城隍神,令神显于吾。”有睢阳小吏,亦预郄事,畏观音奴严明,也惧怕神显其事,乃以任所贿钞陈首,于是罪任商而释孙妾。[35]
在日本古代,神明裁判大多由司法官员主持,神职人员通常也参与神判,所信奉的神为日本固有的神祗。据《贞永式目》“起请”记述:“梵天帝释四大天王惣日本国中六十余州大小神祗,别伊豆莒根两所权现三屿大明神八幡大菩萨天满大自在天神部类眷属,神罚冥罚于各可罢蒙也。仍起请。”[36]为了使神明裁判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司法行政官员充当了监督或见证人的角色。据《倭训刊》记载,元和五年(1619年)九月,在近江国(滋贺县)蒲生郡日野乡的绵向神社举行了一次铁火神判,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日野的东九个村和西九个村因为会权的问题长年纷争,最终决定依靠神判来裁决,幕府和地方诸侯派遣检使役监督。双方在神社前搭起了一个木台,检使役命铁匠对双方的铁斧进行检查,其后,在木台东西两端燃烧炭火,将铁斧烧红,交给双方的代表。东方的代表是喜助,西方的代表为角卫兵。正当两人准备将烧红的铁斧放置手掌时,检使役突然改变了决定,东、西两方代表交换所握铁斧。东村的代表手握铁斧走了十八尺远,西村的代表因不堪忍受铁斧灼伤而逃跑。此次裁判的结果东村获胜。[37]嘉吉三年(1443)八月廿五日,在京都东寺举行了一次神判:“昨日西院落书有之,其子细者定任汤起请手烧之处,验见隐之由有之,仍验见六人召寄被寻闻之处,公文所一人见乎,余人不见之由令申之间,言语道断次第也。”[38]这里的“公文所一人”,是指地方的司法行政官吏。
中国古代的神明裁判有时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选择,没有司法官员和神职人员参加。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律受到宗教的影响有限,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也不高,很少见到有神职人员参加裁判的情况。据清代《玉准输科辑要》卷5记载:瑞州上高县晏月楼,甚刁恶。同治甲子冬,将父遗业出售,召耿富荣向卖。彼时言定价银,书契出票。晏收票照造,存真发假。及契价两楚,复执真票,向荣索取。晏以笔迹为凭,众莫能解。有一乡耆立茂林,生平正直无私,斥晏说:“祇要尔到城隍殿,斩鸡鸣誓,不怕荣不出银。”晏不得已,执一雄鸡,到城隍案前,众亦在侧观之。晏跪地,将欲斩鸡,忽手指颤,鸡两翅高飞,张嘴乱啄,舞爪乱抓,晏被鸡啄得两目流血,乃瞎,痛不可当,大喊说:“城隍责我。’众亦惊骇。晏遂执票交还,荣累始休。”清朝光绪年间撰写的广西《上林县志》记述:“若争斗两不相下,则择显赫神灵叩庙社誓,限日求报。有验者讼即得理,众皆直之。”上述两条史料表明,明清时期的神判有时是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并没有经过司法机关的诉讼程序。
日本古代在幕府后期是政教合一的政权,神社的神职人员在社会上有很高地位。在日本《养老令》中,神祗官居于太政官之前,排在首位,职责是“凡天地神祗者,神祗官皆依常典祭之”。[39]由于神职人员在日本古代社会的特殊地位,凡进行神明裁判,经常有神职人员御子、女巫、阴阳师等参加。据《东寺百合文书》卷112永享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条记述:“去十四日夜,寺家土藏前南方破,代物首尾五十贯分令盗犯了,……仍评议之趣种种有之,仍廿六日于汤屋之前汤起请有之,寺中中房下部以下悉集,于其中危者三人取分及起请文,自七条边御子召请种种有仪式,仍三人去之了。”在本案中,神职人员“御子”主持了神明裁判的很多仪式。
三、神明裁判与中日古代诉讼审判制度之比较
神明裁判是古代证据制度不发达的产物,是在不能确定双方法律责任和过错的前提下出现的。如果凭诉讼证据能够辨明是非,神明裁判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神明裁判在民事和刑事诉讼领域所适用的情况很有限。在民事诉讼审判中,适用神明裁判的情况多出现于买卖、借贷、租赁和雇佣等民事法律行为中;在刑事诉讼审判活动中,适用神明裁判的事例多出现于盗窃、奸淫类的违法犯罪行为中。当人们在民事法律活动中注重书证、人证和物证,在刑事审判中采取疑罪从无和疑罪收赎的原则,提高司法勘验技术水平,选拔高素质的司法官员进行审判,神明裁判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由此可见,创建文明先进的司法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民事、刑律诉讼审判中证据不足的难题,避免神明裁判现象的发生。
(一)古代中国和日本的律令法体系有效解决了诉讼证据不足的问题,使神明裁判的方式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中国古代从战国秦汉之际进入到律令法时代,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隋唐之际达到成熟和完善。古代日本在推古天皇时,由圣德太子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和“冠位十二阶制”,开启了古代日本全面受容唐代律令法的先河,[40]《弘仁格式序》称“国家制法自兹始焉”。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进行大化改新,仿效唐朝的政治体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天智天皇在位期间(662-671),制定了《近江令》二十二卷,文武天皇四年(700),颁布了《大宝律令》,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颁布了《养老律》和《养老令》各十卷,使日本走上了律令制国家的道路。律令制的法律体系有效解决了民事、刑事审判中因证据不足而出现疑难案件的情况,避免了神明裁判现象的发生。
首先,律令制下的民事活动,强调双方当事人注重证据,凡商品买卖、借贷、租赁、雇佣、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民事活动皆须制定法律文书。据《唐律疏议》卷26规定:“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答三十;卖者,减一等。”日本《养老令•杂令》“出举”条规定:“凡出举,两情和同。私契取利过正条者,任人纠告,利物并给纠告人。”[41]近年来在中国和日本各地发现了许多中古时期的法律文书,从文书的内容看,不仅有文书制定的时间,买卖或借贷双方的姓名、标的、违约责任,还有保人和见证人等内容。有了规范的契约文书,在民事审判中就有了充足的证据,司法官员当然不会采用神判的方式。
其次,律令制下的刑事法律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证据不足的问题,在律典中明确规定断罪必须引用国家正式的法律条文。据《唐律疏议》卷30和日本《养老律•断狱律》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答卅。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42]这种近似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本身就是对神明裁判方式的彻底否定。
如果地方司法机关遇到疑难案件,可逐级向上奏谳。所谓奏谳,是指地方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对于事实认定不清或适用法律发生歧义的案件,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允许基层审判机关把所发生的疑难案件向上级司法机关逐级奏报,奏请上级审判机关或中央最高的司法机构裁决。中国和日本古代的法典皆有奏谳的规定,唐令《狱官令》规定:“诸州府有疑狱不决者,谳大理寺,若大理仍疑,申尚书省。”[43]日本的《养老令•狱令》也规定:“凡国有疑狱不决者,谳刑部省。若刑部仍疑,申太政官。”[44]奏谳制度为地方司法机关处理疑难案件找到了一条重要的解决路径,不仅避免了类似案件在各地出现不同判决结果的现象,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还有效地节约了司法成本。古代疑难案件奏谳制度的形成,直接促成了死刑复核制度的常态化。
若确实是疑似难明的案件,可以采取疑罪收赎的原则,让犯罪嫌疑人缴纳铜收赎。中日古代疑罪收赎的实施,是解决疑难案件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里亚指出:“证实犯罪的证据,可以分为完全的和不完全的。那些排除了无罪可能性的证据,我称之为完全的。这种证据,只要有一个,就足以定罪。不能排除无罪可能性的证据,则是不完全证据。这种证据要变成完全的,需要有足够的数量。”[45]受此影响,近代西方的刑法理论通常采取二分法的形式,即分为有罪和无罪。如果证据不充分,则采取疑罪从无的原则。古代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在有罪和无罪之间,又增加了疑罪的概念,《唐律疏议》卷30“疑罪”条对疑罪的含义作了明确的阐述:“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注云:疑,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无证见;或旁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即疑狱,法官执见不同者,得为疑议,议不得过三)”对于疑罪,则采取收赎的原则。疑罪收赎是中国古代基于慎刑和恤刑的观念而创制的,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46]疑罪收赎制度可以避免法官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裁判的尴尬境地,也能弥补神明裁判所带来的错判或误判情况的发生。
在古代东亚的律令法时代,注重选拔高素质的司法官员,认真总结历代司法勘验技术的经验,也能解决一些具体的疑难案件。我国著名法学家燕树棠教授指出,立法、司法人员应具有“法律头脑”,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须要有社会的常识;第二,须要有剖辨的能力;第三,须要有远大的理想;第四,须要有历史的眼光[47]司法审判人员的素质直接决定审判的质量,古今中外许多疑难案件都是依靠司法官员的法律智慧来解决的。先进的司法勘验技术为解决疑难案件提供了方便条件,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封诊式》和南宋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中,都详细记述了古代的司法勘验技术和方法,为司法官员利用已有的司法技术成果解决疑难案件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高度专制集权的政体和司法制度的倒退是中日两国古代神明裁判复活的重要原因
从公元13世纪以后,中国和日木的律令法体系走向了衰败,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得到不断加强。在中国明清两代,废除了战国秦汉以来实行的字相制度,皇帝集行政、军事和司法大权于一身,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顶峰。这种“君尊臣卑”、“君主臣奴”的统治模式严重制约了国家各级司法行政官吏的才能的发挥,对当时的诉讼审判制度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古代日本从13世纪进入到幕府统治以后,幕府的将军统揽一切大权,天皇实际上成了傀儡。在江户幕府时期,颁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17条,规定天皇只许从事学问,不得过问政治,幕府派人监视皇室的活动。庆长二十年(1615),江户幕府颁布了《武家诸法度》,对武士的权利义务、生活规范等作了严格的限制,规定武士不得私婚、不得结党、不得蓄浪人、不得擅自修筑城池等行为。宽永十二年(1635),又严令各地大名“参觐交代”,规定大名必须隔年到江户谒见将军,一年在幕府值勤,一年驻守领地,妻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幕府时期的专制政体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直接造成了日本封建社会后期司法制度的黑暗。
高度专制集权的政体也直接影响了古代中日两国的诉讼审判制度。在中国古代后期的元明清三代,对官吏的选拔不太重视对国家法律知识的考察,司法行政官员的法律素质低下,中国法学进入到了衰败时期。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对中国古代法学盛衰的过程作了认真分析,他认为自从元代废除了律博士之官,明、清两代研究法学之书,世上所知者仅有数十家,“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此法学之所以日衰也”。[48]
元明清三代法学的衰落影响到了当时的诉讼审判制度。在元明清时期的刑事审判中,唐律中“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这种近似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审判模式遭到了破坏。在明清两代的律典中,取消了疑罪收赎的制度,秦汉至唐宋以来形成的疑难案件的奏谳制度形同虚设,地方司法机关在处理疑难案件时失去了解决问题的重要路径。明清两代司法官员的法律责任很大,据瞿同祖先生研究,如果地方发生盗窃、强盗、人命等刑事案件,州县官须在法定的期限内破案和审结,若不能按期破案审结,将会被处以罚俸或降级的处罚。[49]在司法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和面临严厉的法律责任追究面前,审判官员有时采取神明裁判的方式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在民事诉讼审判中,地方司法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可以根据天理、人情和国法进行判决,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指出:“(清代)所有判断都必须根据对国法的解释才能作出”这种思想方法,从根本上是不存在的,而且,并不认为判断必须受每一条法律条文的严格制约。[50]明清两代受儒家“无讼是求”观念的影响,对于地方发生的民事诉讼作了诸多限制,清代每月仅有六至九天专门受理民事诉讼的案件,在农忙季节的四月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凡涉及户婚、田土及各类轻微之事的争讼概不受理。[51]对于轻微的民事案件,通常由乡里等基层组织和宗族邻里进行调解。当调解不成时,则由双方当事人进行盟诅。可见,明清两代神明裁判现象的出现,也与当时社会对诉讼的限制有很大关系。
日本古代幕府时期的诉讼制度不很发达,传世文献的记述也十分匮乏,法律很少有明确的规定。[52]从镰仓幕府以后,司法行政不分,幕府的将军拥有绝对的司法权。在镰仓幕府时期,中央下设政所、问注所、侍所、引付方等机构;地方设立京都守护、六波罗探题、镇西奉行、镇西探题、奥州总奉行等司法行政机构。室町幕府时期,中央管领下设有评定众、引付众、政所、侍所、问注所;地方设有镰仓府,州探题,中国探题,奥州探题,羽州探题,守护、地头等机构,司法行政体制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江户幕府时期,将军之下设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职。大老是特任执行官,属于非常职,由谱代大名中选任;老中是常任执行官,相当于内阁,有四至六人,按月轮值主持大政,负责掌管皇室、公卿、大名、寺社等事务,由谱代大名选任。老中之下设三奉行,即寺社奉行、江户町奉行和勘定奉行。寺社奉行有四人,掌管寺院神社及寺社领地的行政、司法,处理关东八州以外幕府领地的诉讼;江户町奉行二人,分别掌管江户南北两区的行政、司法;勘定奉行,管理幕领内郡代和代官及一般行政、财政事务;在地方的京都、大阪、骏府等地,设置远国奉行,直接行使裁判权。
日本幕府时期没有制定统一的刑法典,《贞永式目》、《式目新编追加》等法令,皆为训令法,并不布告人民,法律处于秘密状态。甚至德川幕府时期的法令,也“布告其命令,而不公示其制裁”。[53。]虽然幕府时期制定了许多法律文件,如《贞永式目》、《建武式目》、《武家诸法度》、《公事方御定书》等;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如江户幕府初期京都所司代板仓父子制定的《板仓氏新式目》,和歌山藩侯吉宗制定的《纪州藩国律》,熊本藩制定的《熊本藩御刑法草书》等,但由于地方司法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除依据上述法律文件外,还可参酌判决例、评议、伺指令等作出判决。[54]武家专权的政治局面和法律的秘密状态造成了幕府时期的刑罚非常残酷。据《贞永式目》第12条“恶口咎事”条规定:“斗杀之基,起自恶口,其重者被处流罪;其轻者可被召笼也。”[55]在安土桃山时期,天正十八年(1590年)幕府颁布了强行检地的法令,规定强行检地,“务须善喻国人及农民同意。必有不愿服从之辈,如其为城主,则驱出城外,喻之不从,则尽杀之可也。如其为农民,不从者,一乡二乡尽杀之可也”。[56]
幕府统治时期,司法制度十分混乱,在民事和刑事诉讼审判活动中,广泛采用起请宣誓的神判方式。所谓的起请,即在神面前对本人及他人宣誓诅咒。镰仓幕府以后,日本起请宣誓的现象非常普遍,镰仓幕府制定的《贞永式目》“起请”条规定:“梵天帝释四大天王惣日本国中六十余州大小神祗,别伊豆莒根两所权现三屿大明神八幡大菩萨天满大自在天神部类眷属,神罚冥罚于各可罢蒙也。仍起请。”[57]
在幕府时期的民事诉讼审判活动中,起请是重要的法律程序。据日本学者中田薰研究,镰仓、室町时期的民事诉讼活动,司法人员(使节)在把传唤状送达被告的同时,也须保证把起请文送达;书面证言要附起请文;在没有书证和人证的情况下,诉讼当事人可把书写的起请文作为诉讼的证据;对实检使复命,也须添加起请文;有关其他所领所课之有无,令当地土著居民作证,须在证言中附起请文。[58]在古代日本的《西大寺文书》卷5“西大寺敷地四至内检断规式”条中,收录了一件盗窃类刑事案件的起请文样式,现抄录如下:
敬白
天罚起请文事
右元者某甲财宝,某甲所盗也(若不知者,都不知之)。若伪申者,日本国大小神祇,殊春日四所别当所,镇守石落神,十五所八幡,三所清泷权现,辨才天、八王子,并四王御影御罚,蒙书手之身,现世成白癫黑癫,当来可堕三恶道者也,仍为后日起请文之状如件。
从该文书的内容看,笔者认为起请文是神誓盟诅的文书化过程。如果双方当事人或证人不如实陈述案件的事实,将会受到诸神的“天罚”。幕府时期的神明裁判,与日本飞鸟、奈良时期律令体制下的诉讼审判制度相比,无疑是巨大的倒退。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古代中日两国神明裁判制度的比较,我们发现在中日两国古代法制文明初期,都有过占卜神判的情况。从战国秦汉至唐宋之际,中国进入到律令法时代,日本从公元7世纪大化改新后全面受容唐代的律令法体系,从《近江令》到大宝、养老律令的编纂完成,古代日本完成了律令法体系的创建过程。[59]在律令体制下,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实行奏谳和疑罪收赎的制度,在民事活动中重视书证的制作,在刑事侦查领域利用已有的先进司法勘验技术,选任优秀的人才担任司法审判人员,这些措施有效地解决了疑难案件证据不足的困境,使古老的神明裁判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从13世纪以后,在中国的元明清三代和日本古代幕府统治时期,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和武人专权局面的形成,中日两国同时出现了诉讼审判制度的倒退,神明裁判在两国古代社会后期又出现了复活的迹象。
中国古代元明清时期与日本幕府时期的神明裁判又有所不同。中国明清两代的皇权一直凌驾于神权之上,宗教对世俗法律的影响十分有限。中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家,当地方司法官员面对疑难案件难以判明时,往往借助于神意裁判。总体来看,明清两代的司法机关审理民事、刑事案件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进行,只有极个别的疑难案件采取神明裁判的方式。在神明裁判的过程中,司法官员居于主导地位,很少有神职人员参与。而在日本古代幕府时期,从镰仓幕府以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融合了中国的朱子学和佛教的思想,丰富了日本的神道理论,使日本走向了政教合一的道路。在镰仓幕府以后,日本进入到以训令法为主的时代,武家的法律处于秘密状态。到江户幕府时期,在老中之下设立的“寺社奉行”机构,负责管理寺院神社和寺社领地的行政司法事务,处理关东八州以外幕领的诉讼事务。寺社奉行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司法行政机构,其地位比江户町奉行和勘定奉行高,拥有更广泛的裁判权,[60]凡是关于神社、寺院领地所发生的诉讼案件归寺社奉行管辖。当司法人员对那些难以判明的民事、刑事疑难案件,由于证据缺失和司法勘验技术落后,往往采用神明裁判的方式。日本古代后期神明裁判的种类很多,实行神明裁判的地点通常选择在神社进行,除司法官员外,寺院神社的神职人员也经常参与,所适用的刑罚非常残酷。
众所周知,法律的最高理想是实现“正义”( Justice ),正义的含义十分丰富,有学者认为它包含“真”、“善”、“美”三种成分。[61]世界古代的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审判方式,它既没有体现法律的“真”和“善”,也没有做到诉讼审判的“美”,是当时法律处于野蛮落后状态下的真实体现。中日两国古代后期神明裁判的复活,表明当时两国的政治制度已十分腐朽,两国的诉讼体制已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如果没有外来法律文化的影响,是很难打破这种固有的法律格局。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全面学习和移植近代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使日本的法律由秘密转向公开,迅速走上了法律近代化的道路;中国在清末也进行了变法和修律的活动,缓慢地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法律转型。
【注释】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本文是上海师范大学第九期校级重点学科法律史学的阶段性成果
[1]宋兆麟:《神明裁判与法的起源》,载《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
[2][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法源论)》,黄尊三、萨孟武、陶汇曾、易家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3]周一良、吴于谨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页
[4][美]孟罗•斯密:《欧陆法律发达史》,姚梅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3页。
[6][日]中田薰:《德川刑法の論抨》,载《法制史论集》第3卷,吉川弘文馆昭和46年版,第729 -752页。
[7]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135页。
[8]夏之乾:《神判》,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版。
[9]杜文中:《神判与早期习惯法—兼及中西法律文化传统比较的一个侧而》,载《法律史论集》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0]吴海航:《日本占代神判法探析》,载《日本研究》2010年第2期。
[11][日]中田薰:《法制史论集》第三卷下,岩波书店昭和46年版。
[12][日]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补订版,第676-701页。
[13][日]曾我部静雄:《关于探汤》,载《日本历史》第80号,实教出版社1950年版。
[14][日]牧野信之助:《关于神誓裁判》,载《武家时代社会之研究》,刀江书院1943年版。
[15][日]伊藤清司:《铁火神判系谱杂记》,杨德芳译,载《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16]同注2引书,第41页
[17][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高鸿均、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18][日]仁井田陞:《敦煌發现十王经图卷に晃之た刑法史料》,载《中国法制研究•刑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补订版,第597-614页;陈登武:《从人世间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6-331页。
[19][日]久宝田:《神道史の研究》,皇学馆大学出版部平成12年版,第4页。
[20][日]中田薰:《起请文杂考》,载《法制史论集》第三卷,岩波书店昭和46年版,第1000页。
[21]《墨子校注》卷8《明鬼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0-331页。
[22]《元史》卷191《田滋传》。
[23][日]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令义解》卷3《神祗令第六》,吉川弘文馆平成8年版,第77-80页。
[24]同注2引书,第22 -35页。
[25][日]三浦周行:《歷代法制の公布と其公布式》,载《法制史の研究》,岩波书店大正13年版,第78页。
[26]新订增补国史大系《吾妻镜》卷43,吉川弘文馆昭和65年版,第560页。
[27]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2-44页。
[28]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日本书纪》卷13,吉川弘文馆昭和58年版,第348页。
[29]《北史》卷94《倭国传》。
[30][日]藤泽卫彦:《日本刑罚风俗图史》,国书刊行会2010年版,第75-77页。
[31]同注15引文
[32][日]中田薰:《古代亚细亚诸邦に行はれたる神判捕考》,载《法制史论集》第三卷,岩波书店昭和46年版。
[33]《元史》卷191《田滋传》。
[34]《元史》卷192《刘秉直传》。
[35]《元史》卷192《观音奴传》。
[36][日]佐藤进一、池内义资编:《中世法制史料集》第一卷《镰仓幕府法》,岩波书店昭和45年版,第30页。
[37]同注15引文
[38]《东寺百合文书》卷153“嘉吉三年八月廿五日”条。
[39]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令义解》卷2,吉川弘文馆平成8年版,第77页。
[40][日]泷川政次郎:《国家制法の始“上宫太子宪法十七侗修”》,载《律令格式の研究》,角川书店昭和42年版;[日]泷川政次郎:《冠位十二階と行の制定の意羲》,载《律令格式の研究》,角川书店昭和42年版。
[41]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令义解》卷10,吉川弘文馆平成8年版,第337页。
[42]新订增补国史大系《律》,吉川弘文馆昭和53年版,第175页。
[43][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栗劲、霍存福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720页。
[44]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令义解》,吉川弘文馆平成8年版,第328页。
[45][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46][日]泷川政次郎:《日唐律にぉける疑罪の溉念》,载《律令格式の研究》,角川书店昭和42年版,第160-172页。
[47]燕树棠:《法律教育之}1的》,载《公道、自由与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297页。
[48]沈家本:《寄文存》卷3《法学盛衰说》,载《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43页。
[49]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214页。
[50][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载《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范愉、陈少峰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51]同注49引书,第196页。
[52][日]三浦周行:《江户時代内裁判制度》,载《法制史の研究》,岩波书店大正13年版,第1041页。
[53]同注2引书,第147-163页。
[54][日]三浦周行:《江户時代の裁判制度》,载《法制史の研究》,岩波书店大正13年版,第1043页。
[55][日]佐藤进一、池内义资编:《中世法制史料集》第一卷《镰仓幕府法》,岩波书店昭和45年版,第9页
[56]《日本史史料演习》,第204-205页,载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集•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55页。
[57][日]佐藤进一、池内义资编:《中世法制史料集》第一卷《镰仓幕府法》,岩波书店昭和45年版,第30页。
[58][日]中田薰:《起请文杂考》,载《法制史论集》第3卷下,岩波书店昭和46年版,第966页。
[59][日]泷川政次郎:《律令内研究》,刀江书院昭和41年版,第53-248页。
[60][日]三浦周行:《江户時代の裁判制度》,载《法制史の研究》,岩波书店大正13年版,第1050页。
[61]吴经熊:《正义的探讨》,载《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5页。
(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