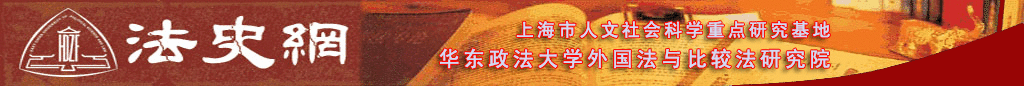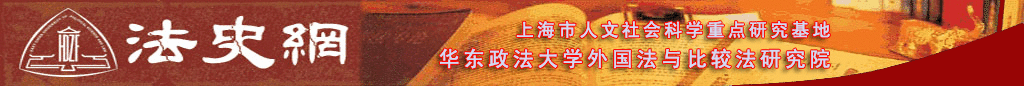作者简介:
郭威,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8;东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讲师。哈尔滨 150030;从事法理学研究;应星,男,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法社会学研究。北京 100088
原发信息:
《求是学刊》(哈尔滨)2016年第20161期 第96-103页
内容提要:
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论者对古典自然法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将个体自然权利置于公共善之上。帕森斯认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将自利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政治强制来加以解决,从而避免了霍布斯式自然权利对社会的摧毁。哈奇森通过对人性的重新理解来对霍布斯加以反驳,并指出人性中的道德感使人自然地就具有社会本性,并能自然地将人类的普遍利益作为公共善置于个人自然权利之上,政治社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求人类的普遍幸福。哈奇森关于道德感与自然权利的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natural law theorists,Hobbes makes a revolutionary change of classical natural law in placing the natural rights of individual over the public good.Parsons believes that "Hobbes‘s problem of order" which contains a tension between self-interest of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is resolved through political force,thus avoiding the Hobbesian natural rights to destroy society.Hutcheson refuses Hobbes‘s idea wit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and points out that moral sense in human nature makes man natural to society.Moral sense naturally makes the general interests of mankind as public good over individual natural righ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 society is for the pursuit of universal happiness of mankind.Hutcheson‘s idea of moral sense and natural rights provides an important clue to our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关 键 词:
道德感/公共善/自然权利/Moral sense/public good/natural rights
一、现代自然法与“霍布斯的秩序问题”
无论是从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上来看,还是从思想学术的意义上来看,自然法思想对西方的法律、道德、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法学者将自然法看作是一切法律、道德、社会与政治观念的渊源,通过自然权利这一核心范畴将个体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古典自然权利论者主张,人的天性或人的自然构成决定了人的善的生活就是与人的存在的自然秩序相一致的生活,人天生就是社会的存在,人性本身就是社会性,人的社会性构成自然权利的基础。自然的完善是人的首要义务,为了这个目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基本的道德事实是善先于权利。人具有理性能够认识到自然法、自由的范围,并通过理性形成正义、节制等德性。政治社会优先于公民个人。[1](P129-131)在17、18世纪发展起来的现代自然法理论完全颠覆了古典自然法理论,将个体置于整体之上。[2]
格劳秀斯被视为现代自然法世俗化的第一人。他指出,人的本性是自利的,人为了自我保存而热爱社会,因此,人的本性中也具有社会性的一面。自我保存是原初的自然原则,是和自然法相一致的首要义务。为了这一首要义务的履行,产生了各种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源于人的理性,是指本身是正当的东西。自然法是正当理性的命令,是人为实现自然法的目标而具有的一种道德特质,是一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3](P21-24)而真正对这一颠覆作出革命性变革的是霍布斯。霍布斯拒绝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的命题,并驳斥了格劳秀斯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观点。在霍布斯看来,人是现实的存在物,是各种自利欲望的集合体,处于各种欲望顶端的是自我保存和避免死亡的欲望。人根本就没有天然地应当去追求的自然目的或善,“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极终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地发展,达到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人类欲望的目的不是在一顷间享受一次就完了,而是要永远确保达到未来欲望的道路。……因此,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4](P72)。人为了获得财富、荣誉、统治权等权力欲望的满足而彼此争斗,为了达成自己的欲望所采取的是杀害、征服、阴谋诡计,德性只不过是为了自我保存的理性手段而已,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所谓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4](P97)。这样的自然权利将自然物都看作是人的支配物而存在,国家制定法的本质就是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规定,一切都以个体的自我保存为圭臬。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清晰地看到了霍布斯式自然权利所带来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指出,新教改革剥夺了可能威胁个人自由的古代异教国家的神圣性,国家只有在对个人的宗教利益有所裨益或至少是并行不悖时,才得到宗教的赞许。新教这种将宗教的价值置于个人之中的独特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新教赋予了个人向权威争取自由的规范性;另一方面,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往往是经验性的和实际的,原因在于强调以宗教名义获得的自由可能会被滥用从而危及社会本身的稳定。[5](P98-99)在新教改革后,在个人自由的神圣性与政治国家的事实强制性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帕森斯指出,当社会思想在17世纪变得世俗化的时候,它的中心问题是社会秩序的根据问题,尤其表现为在与国家强制性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权威性控制之下的个人自由的范围问题。对个人自由的范围得到了规范性论点的证明和保护,首先是出自宗教自由的良心自由的论点,后来是自然法的世俗形式的论点,这种自然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合乎道德的绝对的自然权利。与这种规范性论点针锋相对的是为权威辩护的论点,指出人必须和他的伙伴一起生活,并将罪恶看作是“自然人”的决定论本性。[5](P99)在帕森斯看来,后一种观点的典型例子就是霍布斯。由于人在霍布斯这里是受激情驱使的,人们在寻求各自的目的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是霍布斯的思想基础,人们达到各自的目的的权力就是划分界限的根源。帕森斯指出,霍布斯的理论体系几乎纯粹是自利性的,如果按照严格自利性主体的假设,霍布斯所说的“战争状态”根本就不是一种秩序,而是混乱,在霍布斯的实际秩序中不存在合理性和目的性这两种规范性特征。作为实际秩序,纯粹自利性个体的结果只能是混乱的和不稳定的,不可能在经验上存在。由于权力处在社会秩序的中心,这种社会对个体使用什么手段没有限制,社会必然会分崩离析,陷入无节制的权力斗争当中,满足霍布斯称之为“激情”的终极目的的前景统统被葬送了。[5](P104-105)
帕森斯指出,霍布斯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他的理论中的困境。既然在自利个体之间无法达成秩序,于是霍布斯就将合理性扩展到理论的其他方面,直到行动者认识到自身所在的处境是一个整体。霍布斯所提供的最终的解决办法是社会契约。人的激情只能带来彼此的战争与阴谋诡计,但是,人的理性发现了自然法,为了避免毁灭,人们在理性自然法的指引下达成社会契约,建立强大的政治国家——“利维坦”来维持社会秩序,确保彼此目的的实现。利维坦是基于个人的授权而形成的人为的人格,是一种“人造人”,它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我判断善恶的自由、人的自然权利、理性自然法都被国家的制定法所取代,臣民的自由只有在主权者未对其行为加以规定的事物中才存在[4](P164)。
在苏格兰学者中,较早对“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提出有力批评并提供解决方案的是弗兰西斯·哈奇森。他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利维坦这一人造物,自利的个体如何共存于社会秩序当中?自然法是否就应当彻底沦为国家权力的附庸?人的自然权利是否仅仅同人的自利欲望的满足相关?哈奇森提出的自然法体系旨在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寻求一种一致,不求助于利维坦,而是通过人性中的道德感这一自然禀赋使自然法成为人类社会的实质性的道德律;人的自然权利并不是仅仅为了自我保全欲望的满足,人性中对普遍善的追求先于自然权利而存在,对普遍善的义务先于自然权利而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正是哈奇森的努力,使自利的个体与公共利益取得了一致,而且使人类的自然权利避免了主观的抽象性,并对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权利的自然史以及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道德感、人的社会本性与普遍自然法
霍布斯将社会秩序问题建立在人的绝对自利本性之上。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更是将人的自利本性发展到了极致。曼德维尔指出,社会就是一个由无赖、流氓等组成的“邪恶的蜂房”,正是个体的恶德促生了公众的利益。[6]通过霍布斯和曼德维尔的影响,“人的本性是自利”似乎成了人性的唯一标签。
1729年12月,哈奇森被聘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1730年11月,在他正式进入大学之际发表了题为“论人类的社会本性”的就职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指出,许多近代作家没有充分回答什么是能被正确称为人类本性的一般问题,以及我们的社会本性在于什么的特殊问题,最后是我们用我们本性中的什么部分正确提供和走向社会的问题。这些作家似乎是从人类最坏和最可耻的角度描述人类本性。[7](P209)哈奇森所指的“近代作家”正是霍布斯、曼德维尔等人性自利论者。为了反驳霍布斯、曼德维尔等人的论点,在哈奇森看来,正确认识人性的构造是根本的出发点,哈奇森在借鉴沙夫茨伯里的道德感和洛克的感官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人性构造的感官理论。他指出,人的本性中存在着外在感官、内在感官、道德感官、公共感官和荣誉感官。人通过外在感官接触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外在的对象并产生快乐和痛苦的感觉,包括听觉、视觉、触觉等,人的肉体欲望就是源自外在感官。内在感官能知觉到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秩序的美,能知觉到其中的规律性、一致性,并使人产生愉悦的感觉。公共感官是每个人都会“因他人的幸福而快乐,因他人的苦难而不快”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并不考虑自我利益的情况下也会产生。道德感官能使我们知觉到他人情感或行为的道德上的善与恶并据此作出道德判断,正是由于道德感官产生的道德感的存在,我们才能在各种各样的情感和行为中去选择道德善,并对他人进行道德上的判断。当我们做出道德善或道德恶的行为时,荣誉感官会给我们带来荣誉感的快乐和羞耻感的痛苦,即使没有自我利益的考虑,我们也会追求荣誉。人的感官给人带来快乐或痛苦的知觉,人的心灵就会产生对快乐的欲望和痛苦的憎恶。同感官的类型相一致,人的欲望或憎恶也可以相应地表现为五种类型:由外在感官产生的对肉体快乐的欲望以及对痛苦的憎恶;内在感官产生的对美的快乐的欲望以及对丑陋事物的憎恶;公共感官产生对公共幸福之快乐的欲望及对源自他人苦难之痛苦的憎恶;道德感官产生对德性的欲望及对恶行的憎恶;荣誉感官产生对荣誉的欲望及对羞耻的憎恶。欲望就是激情,是没有理性指引的;当欲望获得了理性的指引就转变为感情。但人的行动往往被激情所左右,由欲望或憎恶所推动。
哈奇森通过对人性构造的分析试图说明:人性中的感官构造使人既能关注自我保存,同时还能无私地关注他人的幸福与否。在《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中,哈奇森专门对美与秩序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在他看来,上帝创造了自然界,在自然界中到处存在的一致性的美表明上帝是仁爱的,而非严酷的惩罚者。既然上帝是仁爱的,人的本性也应该是仁爱的,人追求最大幸福的行为在本性上具有巨大的道德必然性。[8](P76-78)人的行动是由感官所产生的欲望和憎恶支配的,从本性上来看,人会选择追求快乐并避免痛苦。在不同的感官所带来的快乐和痛苦之间,外在感官所满足的快乐最短暂,道德感官所带来的快乐最长久,因此,从总体上看,人的本性应该是趋向于道德快乐的,应该是仁爱的。哈奇森指出,从道德善的角度来看,公共感官、荣誉感官最终都与道德感官相一致,对德性的欲望可以说是人性中最高尚、最长久的欲望。因此,在哈奇森看来,人的仁爱情感推动人去爱他人,而道德感官能够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上的判断,道德感就是人的良心。德性是存在于人的情感中的人的本性,而非理性反思的结果。理性只是提供了选择的手段和设计,最终推动人去过一种德性生活的动力是人的道德感官。通过道德感官,我们就能够形成公正、节制、坚忍、审慎的德性。[9](P206)这是走向我们本性上的至上幸福之路的道德要求。
在哈奇森看来,自利的个体能够在社会中并存的原因,就在于道德感为个体确定了规范性,道德感能够使人产生对正确(right)与错误(wrong)的看法:个体的行为凡是倾向于公共利益或者倾向于与公共利益相一致时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这样一来,通过人本性中的道德感能够在自我保存与关注他人幸福之间寻致一种平衡,并最终以人类整体的幸福作为自身情感和行为的规范。按照哈奇森的见解,这种规范性的体现就是自然法,而道德感正是自然法的基础。“道德哲学的意图是把人们引向最有效地倾向于促进其最大幸福和完善的行为指南;用不着借助于任何超自然的启示,通过从人性的构造中所能发现的各种观察和结论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些行为准则或规则被认为是自然法则,它们的体系或集合被称为自然法。”[9](P3)因此,自然法从根本上来说是在人性构造中所天然具有的道德律法,人自然而然就具有的道德能力,而非源于上帝的启示,也非源于统治者的强制灌输。
在现代自然法理论中,普芬道夫认为,人的向善意志是来自于上帝的赋予,自然法体现人的社会性的道德义务。[2](P338)哈奇森追随普芬道夫的脚步,将社会性作为人的本性,通过道德神学的温和主义否认人类堕落后只存在自私的性情,但他用一种情感式的道德实在论指出人性中自然就具有向善的道德品质与能力。由于自然法是心灵原初的道德规定,是人类通过对自然构造的推理和反思得出的明智结论,这些结论显示出哪些行为是有价值的和有益于公共利益的,因此,自然法是完美的、永恒的和不变的。从人性构造中可以看出,“爱上帝,促进普遍幸福”[9](P253-256)就是普遍的自然法。这是上帝和自然推荐给我们最美好,也是最有助于人真正幸福的生活指南,是从人性构造和观察中所能建议的最明智的追求人类普遍利益的方式。[9](P213)
三、自然权利先于善还是善先于自然权利
现代自然法论者普遍将自然权利的正当性建立在人的欲望的正当性之上。而在哈奇森看来,格劳秀斯式的主观自然权利并没有逃离有悖公共利益的可能性,个人的欲望的满足有可能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格劳秀斯式的自然权利的关键就在于,他没有以道德观念作为人类情感和行动的前提,他的权利观念中缺乏对人类最广泛利益的尊重。[9](P239-240)而霍布斯式的自然权利出发点则是对人性错误的判断。
哈奇森赞同普芬道夫式的自然法和自然义务理论。普芬道夫将人的社会性优先于人的自利本性,认为人类的基本特征虽然是对自我保存的不断关注,但由于人性自身的弱点,为了安全,人必须要社会化。这种社会性法律——教导一个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有用成员的法律——就是自然法。[10](P82-85)在哈奇森看来,普芬道夫所提出的自然法理论认为恒常的仁爱和社会行为是提升每个个体自然善的有效手段,也是以整体的义务为先。[8](P19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奇森赞同普芬道夫的观点,并以普芬道夫的自然权利为摹本将道德实在论同自然权利体系相结合,提出了一种以公共善为指向的自然权利理论。
哈奇森认为,人性构造中天然地具有道德感,共同善是每个人的本性中所包含的内在道德倾向,在人的本性中就具有一种毫不在乎我们自己的利益而赞同并履行为了公共善的行为的自然禀赋。因此,实现公共善的人类本性必然产生人类走向仁爱的义务,这种义务是由人的道德感官所决定和保障的,只有这样,人才能够是快乐的。[8](P191)普遍自然法就是这种道德观念的体现。在哈奇森看来,既然人性中通过道德感官我们就能获得关于善恶的观点,这样的道德实在论的结果就是不用凭借人法的强制或神法的启示我们也能获得对与错的看法。然而,道德感官所判断的是“对”而不是“法”,“法”是跟着“对”而产生的。[9](P236)自然法相比较人性而言,是根源于人性中的道德感的,自然法的根本目的是顺应人性的必然性去实现共同善,因此,自然权利作为某些人能够胜任的道德属性就只有在道德感官认可的情况下才能成其为权利。自然权利是从自然法中衍生出来的,“事实上正是为了社会利益,我们每一个天赋的愿望与感觉,甚至是最低类型的愿望与感觉,只要它们的满足与较高尚的满足相一致,并正确地隶属于它们,它们就应得到满足”[9](P238-239)。这样的每一种愿望和感觉似乎都有一种天赋的权利观念伴随它们。权利的前提在于我们要形成道德观念,这样我们就认为我们有权利满足它们。这种绝对的权利感(sense of right)似乎是自由感(sense of liberty)的基础。[9](P239)权利意味着自我满足的绝对自由,而自我满足的前提是公共善,对公共善的义务始终是先于人的权利而存在,公共善是人的道德感官的本能,这样的对公共善的义务是出于对上帝的感恩而履行的义务。这样一来,普芬道夫式的自然义务被哈奇森转变为通过内在感官和道德感官感觉到的对上帝的义务、对公共的义务,这样的义务不是由上帝所强加的,而是人的自然禀赋所自然孕育的。自然法被理解为内心的道德决断以及从那些决断和其他自然观察中所推导出来的结论。[9](P252)自然权利是为了实现人性中的固有目的而形成的自然而然的权利。
哈奇森以道德感官推导出自然权利观念:某人在某些境遇中普遍为人所允许的施行某种行为以及命令或拥有某物的能力,只要它们“在整体上趋于总体善”,某人就具有相应的权利。根据公共善趋向的强弱,这种权利就有大有小。[8](P198-199)只有趋向总体善的权利才得到道德根据。从公共善出发,哈奇森将权利分为“绝对权利”(perfect right)和“非绝对权利”(imperfect right)。“绝对权利”是指如果它们受到了普遍侵犯就会使人类生活变得不堪忍受。它包括生命权利,财产权利,名誉权利,身体完整和健康的权利,获得诚实劳动成果的权利,这是人的天赋自由的体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非绝对权利”是当它们受到普遍侵犯时,它们不会必然使人痛苦不堪,这些权利会趋于改进或增加任何社会中的肯定的性的善,但不会绝对必然地阻止普遍的痛苦。如穷人所拥有的接受富人施舍的权利。从对共同善的促进角度来看,绝对权利在实践上要优于非绝对权利。绝对权利关乎个体的生存,更关乎社会的普遍利益。
哈奇森还详细分析了人所拥有的其他自然权利。[11]他强调,每一种权利都存在着相应的责任(obligation),责任不是来自于统治者,而是来自于我们的道德能力。由于上帝掌管人类事物,所有的理性创造物服从上帝的意志也是有益于人类的普遍利益的。于是,人所拥有的终极权利是那种趋向于普遍利益的权利,我们的权利其实就是对上帝的责任,为了我们对上帝的责任,我们才拥有权利。权利仅仅意味着利益的观点并不能证明自己所宣称的权利是有益于普遍利益的或者是与普遍利益相一致的。[9](P249)
哈奇森延续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传统,强调义务先于自然权利,并用道德感取代了霍布斯与普芬道夫自然法中的理性,通过道德感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影响所推导出的自然权利观念,将公共善的义务置于自然权利之上,霍布斯式的原子论的社会法律思想以及普芬道夫的社会性自然法思想被一种人类的集体观点及共同善的观念所取代,自然法不是为了个人自保的理性自救,自然权利也不再具备满足个人私欲的正当性,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转变成基于实现人类整体利益的源于人类本性的道德律法,上帝是这一使命完成的最终保障。
四、国家法律的本质与“理想国”
罗门指出,在霍布斯这里,十分悖谬的是,自然法成为一种无用之法,被压缩为关于顺从的社会与治理契约的法律形态,自然法仅有一条基本的规范:“必须遵守协定。”除此之外,就仅剩下主权者的意志了。经过霍布斯之手,自然法乃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一套伦理体系的那种古老观念已丧失了功能:即充当实证法的道德基础;给人们提供一个判断实证法之正义性的标准和规范;体现一种历史地存在的国家——作为立法者与正义的守护者——应当追求的永恒理想。[12](P78-79)
在哈奇森看来,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这一主观的心灵构造需要现实中的国家来具体保障与实现,但是,这种国家不是人为的利维坦。
哈奇森指出,人类存在着原初的自然状态,但是这种自然状态由于人的社会本性的原因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状态。人的道德感使人自然地具有为了公共善而行动的道德倾向,因此,自然状态不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是一种和平状态。自然法就是这种状态下的法律。[9](P264-265)
由于道德感对约束人的情感和行动的软弱性,道德易错性始终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各种自私自利的爱好与感情过于强烈,时常会突破道德感的防线,人类的道德败坏使公民社会即国家政体的组建就显得尤为必要。哈奇森指出,国家不能建立在暴力之上,也不能建立在上帝神秘的启示之上。组成国家政权的唯一的自然方法必须是人们的某种契约或协定。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普遍的幸福。因此,在哈奇森看来,国家政权的建立主要在于两个条件:人们的同意和能促进人们的普遍幸福。[11](P211-212)为了防范人性中的道德易错性,哈奇森在综合了各种政体的长处并避免短处的经验分析之后,提出了一种混合政体论,这种政体既能保证掌握国家权力之人的智慧,同时也能具备对民众的忠诚,处处体现了权力的制衡,并以良好的自耕农作为土地的所有者。[11](P239-244)只有这样的国家政体才能促进人们的普遍幸福。
国家的一切法律的目的都旨在民众的普遍利益和幸福,而这又主要依赖于民众的美德,因此,通过一切正当和有效的方法发扬真正的道德原则是立法者的事。[11](P279)法律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训诫,用以说明被要求或被禁止的行为;一个部分是奖励/制裁,说明对服从所给予的奖赏或对违反所施加的惩罚。所有明智与公正的法律要么倾向于社会的普遍利益,要么倾向于与普遍利益相一致、有益于普遍利益的社会的某部分利益。人们服从法律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出于对立法者的恐惧,而是通过服从所带来的道德上的好处或者直接指向由法律所建议的那种有益的目的,或者在于向立法者表达感激之情。[9](P250-255)
将公共利益作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是符合人性道德感的必然结果,为了能够将个人的道德自主性转变为社会性的道德结果,立法的主要目的是要先进行教育训练和指导,奖赏正义、节制和一切符合社会的性情。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提供良好的教育,教化人们的道德感;掌权者以身作则并任命有德性的人来担当高官。法律要鼓励勤劳、节制、公正和坚忍,反对奢侈和放纵。国家法律的要务就是:强化自然法;指导民众以最佳的方式行使其权利,规范他们以最审慎的方式从事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惩罚对公共利益的犯罪等等。[11](P292)这就是对普遍自然法的规范性要求转化为制定法上的内容。但哈奇森指出,普遍自然法并不能被想象成不变的,还存在着一些异常的例外情形,这些异常的例外情形是通过观察在一般情况下什么类型的行为对社会是有用的而得出的结论。在异常情形中,为了普遍利益,人们会违背自然法的一般规则而不是遵守一般规则。有时候,明智的人类法律可能会剥夺或限制一些从前由自然法使之神圣有效的属于个人的权利。所有的异常情形下的例外都源于特别自然法,在异常必要的情形下,通过明智的法律制度,我们所有的权利都受到限制:与遵守普遍自然法相比,所有这些例外的制度倾向都被证明是有益于更高的社会利益的。[9](P255)特别自然法并不是对普遍自然法的违反,两者在对社会利益的维护上是一致的。
从总体上看,统治者的主要任务、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国家法律就是彻底实现了自然法,而自然法的根源就在于人的道德感官,公共善作为人的道德目的是人类的人生责任和最高目标,哈奇森实现了将国家法与自然法的二元结构在最终的目的上的一致。这样一来,一个完美的道德统一体就此形成了。
波考克在分析西方财产观念的历史变化时指出,古希腊的财产是人的政治属性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的前提,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在17世纪,霍布斯论述财产的方式将人的自我保存的欲望抬升至最高位置的结果是人彻底变成了万物的主宰,万物都是为了人的欲望的满足而存在。他指出,霍布斯开创了个人与物之间的自然权利,自然状态下的个人将他们的权力扩展到物,强调的是个人对占有物的权力,从而使人从占有以前的时代进入占有的时代。[13](P152,156)而这样的观念被曼德维尔所进一步强化,这是新的经济力量得到承认和自我肯定的重要表现。
但在哈奇森看来,霍布斯和曼德维尔式的人与物的权利观最终会压倒政治上的稳定,人的贪婪、道德上的腐败都会导致社会的解体。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哈奇森通过道德感所产生的共同善观念使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哈奇森采取了柏拉图道德理想国的外壳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形式,将公共善作为人的自然目的并上升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用自然法将公共善与政治国家联结起来。道德自律的个体使自然权利并不仅仅具有私人领域的意义,而且具有公共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并不仅仅只是人与物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其实从自然法来看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服务的。
施特劳斯将由马基雅维利开启并由霍布斯推向高峰的“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的主要特质归纳为“将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与“设想自然必须披上作为单纯的人工制品的文明产物的外衣”,在“存在”与“应当”之间画出了一条明确的界线,并将“应当”俯就“存在”。作为对第一次浪潮的回应,卢梭批判了科学与技术以及自然的人工制品,并以古典共和国的非功利性德性的名义对抗霍布斯等人的主张,并认为人的本性不能归因于自然,而要归因于历史过程,并用普遍意志去取代自然法,“应当”的根基无论如何也不在“存在”之中。卢梭的自然法理论将普遍性与历史性作为对霍布斯的反动,对欧陆的历史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14]
哈奇森看到了霍布斯秩序问题中包含的紧张,他提出人的社会本性,认为人对共同善的义务先于人的权利而存在,其目的是运用自然法这一“实质性内容”去克服紧张,只不过他并没有选择理性,而是选择了人的情感作为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基础。共同善是人的本性的内在规定性,政治社会的起源就摆脱了想象中的政治强制力,国家的目的与自然法的目的是一致的。以人的情感为核心,从人的自然禀赋中寻求自然道德律,将人的主观自然权利转化为一种带有客观性的自然权利,“存在”重新俯就“应当”。
哈奇森的道德哲学对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中反唯理论的特色,在道德上对感觉和情感的重视,在社会理论上提出不同于政治社会的“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概念,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正是得益于哈奇森的理论贡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不同于欧陆的思想启蒙之路。休谟指出,道德的区别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道德感。但休谟并没有完全遵循哈奇森的路径,他更看重在人类的自然史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他从经验中指出在权利和义务的起源中也包含着很多人为的措施和发明的标记,即使是为了公共善的目的,有些权利仍然是人为的。[15](P29)受哈奇森影响最大的是亚当·斯密。斯密保留了哈奇森对人的社会本性与自利本性的区分,并接受了哈奇森所指出的道德快乐高于肉体快乐的论点,但斯密的理论比哈奇森更世俗也更加科学。[16]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同情机制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性的纽带,并加入了中立旁观者作为道德判断的裁决人,并引入了“良心”消退了哈奇森道德感的不确定与神学色彩,增强了道德机制的科学性。斯密在《自然法理学》中明确指出,自然权利的起源就在于同情和中立旁观者。[17]斯密将自然权利置于人类社会自然进程中,用人类的文明社会史取代了自然状态的虚构,自然权利与法律的历史也就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对自然权利、对法律的发展与变化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类的技艺(art)的进步。在《国富论》中,斯密充分肯定了人的自利本性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但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斯密认为哈奇森意义上的公共善并不是人的自然目的。所谓的公共善的实现,是在自由制度中,尊重自然权利,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实现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意外结合
原文参考文献:
[1]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2]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2015.
[3]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6]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肖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弗兰西斯·哈奇森:《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人类的社会本性》,强以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8]弗兰西斯·哈奇森:《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高乐田、黄文红、杨海军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9]弗兰西斯·哈奇森:《道德哲学体系》(上),江畅、舒红跃、宋伟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0]塞缪尔·普芬道夫:《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鞠成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1]弗兰西斯·哈奇森:《道德哲学体系》(下),江畅、舒红跃、宋伟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2]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13]波考克:《德行、商业和历史——18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论辑》,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14]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译,载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15]努德·哈孔森:《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赵立岩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6]王楠:《亚当·斯密的社会观:源于人性的自然秩序》,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文章来源:《求是学刊》(哈尔滨)2016年第20161期) |